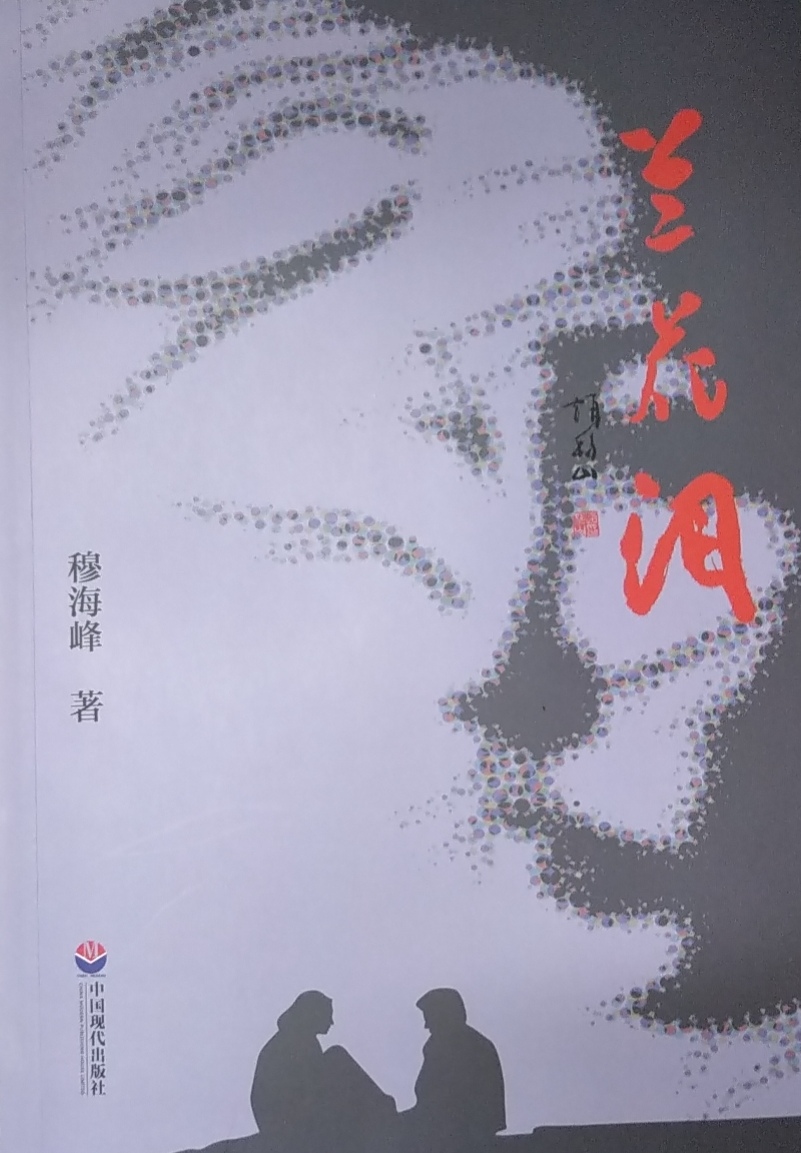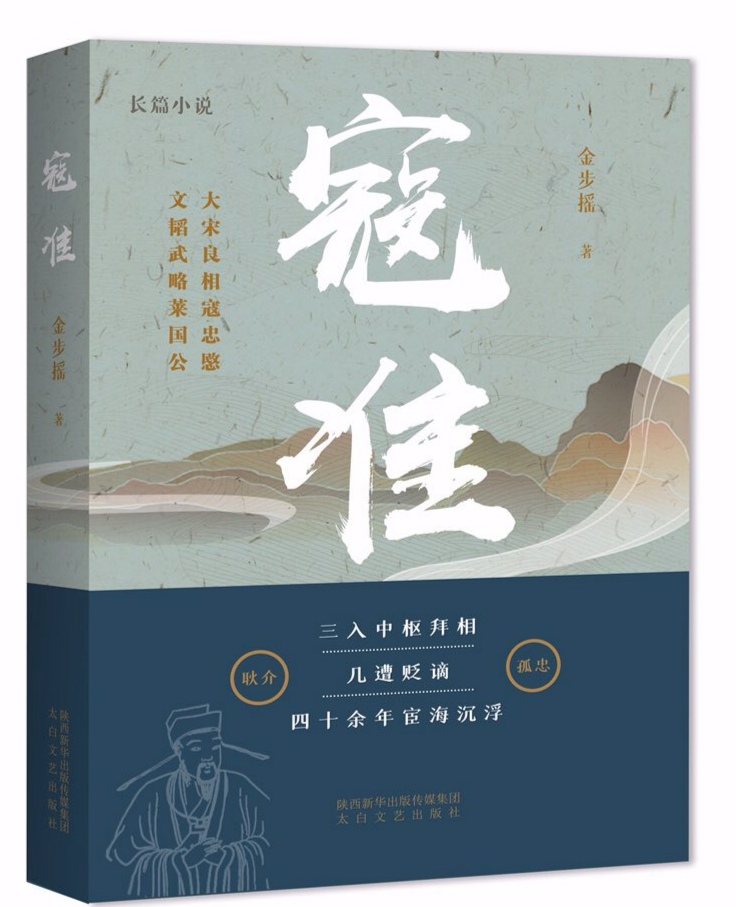穆海峰
小灶房并不大,紧挨着红色油漆大门的北侧依围墙而建,南北较长,靠大门内墙装有一小木门,进了小木门,有一米左右的小过道,过道较窄,仅容一人进入;过道尽头,就是南北狭长,东西窄小的内室了。灶房长约三米,宽约两米,靠东墙上方有一两尺左右的小窗,用来通风和采光,一缕阳光透过窗外的屋顶,直直的照射在脚地上,成一歪斜的方型图案儿。
这里明显住过人,西墙上有贴过年画的痕迹,南墙边动过烟火,显然烧过饭。我们是这里的第几位穷住户,不得而知。无论如何,条件再差,对于我和父亲,这来自穷山村的土得掉渣渣的农家住户来说,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谈论的了。相反,只要在这大城市能有个窝,比起外面垃圾堆里的叫花子,这应该就是能遮风避雨的人间天堂了。很快,我同父亲用院子墙角里的碎砖头块儿,垒了南北两边的床脚,将我们买的简易双人竹板床架上去,铺了铺盖卷儿,窗子靠南脚,支了蜂窝煤炉子,再支起一小木板,摆放了锅碗瓢盆。父亲从外面买了二百多块蜂窝煤,又拉着我去东八里村边的一家机关大院里报了美术班,从此以后,我的心就落在了那里。
学画的生涯开始了,每天,父亲一大早就拉着架子车去康复路瓜果市场进货。而我,一个人拿着历史、政治、英语、语文等高考教辅资料,在窗子下反反复复地读着记着。每当头脑发胀的时候,我会爬在窗子上,看对面屋顶上偶尔飘过的形态各异的白云,听窗前梧桐树上几只麻雀甜脆的鸣叫,低声学外面不同商贩的叫卖之声。
每当太阳爬上了一家工厂的黑色大烟囱,我知道已经到做早饭的时候了。先从院子用小盆打来水,倒半锅的水儿,打开火炉子,看着那蓝色的火苗从炉子里溢出来,静静地舔着锅底,我就会从面袋子里舀出半碗包谷臻子,倒进一汤勺碱面去,待到水在锅里起了浪花,左手掐紧碗沿,不住地抖动手臂,让包谷臻子均匀地散落在浪花里,右手握了勺把,不住地沿着锅壁划着圈子搅动,正几圈反几圈,直搅到那铁锅里看不到面疙瘩,而是均匀一色舀起成线的金黄稀饭儿,到了那香甜的苞米味儿直扑向鼻孔,这时,才盖了锅盖儿,关了炉火让炉下的余温再让稀饭焖上数分钟,苞米稀饭就大功告成了。这时,我会从菜坛子里捞一把酸菜来,挤去汁水儿,用菜刀切碎了,撒上盐、花椒面、辣椒,在火炉上熟小半勺油泼了,然后锁上门儿,到西八里村口去,远远地眺望着小寨方向的马路口,焦急地等待着老父亲的归来。
每当父亲拉着架子车的身影出现在村口的树荫下,我会急跑过去,帮父亲拉车。那一刻,父亲是驾车的老黄牛,而辕边牵绳的我,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小牛犊。我们很快就到了家,父亲笑呵呵的将几个热腾腾的大蒸馍塞到我的手里道,“潮生,饭好了没?”“好咧!”我大声回道,并将一条早已打湿的毛巾拿在手里,等着父亲擦汗。父亲卸着货,满脸堆集着开心。我知道,他在偷偷高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己的孩子长大了懂事了。
每次,看着父亲香喷喷地喝着稀饭,大口大口嚼着我做的酸菜,对我竖着布满茧子的大拇趾时,我都会幸福的不知道说什么好。说句心里话,我应该感谢父亲,当我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之上,左右徘徊,不知道回家务农,还是继续上学,逐我遥远的大学梦。是父亲站了出来,他本来在长乐坡卖水果,当他知道我喜欢画画时,他拉着架子车,一边买水果一边打听,当他来到八里村,知道了美院教授办的美术培训班,知道了每年有不少学生从这里走进了心仪的大学,他心一横,决定伴我一起,去圆我的求学之梦。六十多岁的老人啊,拉着架子车,每天行程几十里,风里来雨里去,行走在城市的夹缝里。感谢父亲,是父亲将我引到了正确的人生大道上,知道了什么是素描、速写、色彩和创作。使我从零开始,并一点一滴地提高。
吃过早饭,父亲拉着水果去周围转乡,而我,则背了画夹,早早地来到画画的地方。这是一个机关大院,平时人不多,院子里停了几辆各色的小轿车,除过十几个工作人员外,就是我们这几十个学画画的孩子了。我们的教室在靠南边四层小楼的二层上。靠东边是一个大教室,南北采光都很好,教室东边摆了几组静物,是我们写生画色彩的地方,中间靠北边的墙壁下,摆放了两张课桌一条方凳,是模特坐的地方,围绕那条方凳,用条凳和课桌,围了两个半圆弧儿,条凳在内课桌在外,这样,外围高而内围低,错落有致,这是我们画速写的地方。
教师都是美院的教授和讲师,教师不固定,经常轮换。每天两个小时的专业课,速写、素描、色彩、创作交替进行。学生的位置不固定,谁来得早,谁就会占据自己最喜欢的位置儿,迟了,就只有委屈自己,选择地儿机会就较少。所以学生来的大多都较早,我是来得最早的几个学生中的一个。
速写老师是个大胡子高嗓门的中年人。第一次上课,他让我想到了《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来。但细细想想,老师除过胡子没有张飞的长,其他方方面面,还真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版的张飞了。我相信,只要稍加装点,老师一定能胜任张飞这一角色。每当我们认真的画速写时,老师会盘腿坐在中间的条凳上,斜靠了北墙,瞪大了双眼环视着四周,谁不认真开小差时,他都会第一时间点你的名,让你注意,在这一点,谁在有办法,也别想逃过他的法眼。在速写班,我的速写进步最快,每次,当老师将我的作品展示在前排时,我都激动得不得了,我相信那一刻,大家的眼光都在齐刷刷的盯着我,我的脸色那一刻会发红发烫,心跳加速,怀里像踹了一个兔子一样。
素描老师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圆脸,头发较长,整整齐齐向后梳去,包了多半个后脑勺。人较胖,圆肩膀圆胳臂圆腿圆手,啤酒肚,好穿一件黑色的宽松体恤衫,说话比较甜,但画画底子深,没有架子,并准时到位,从不迟到早退,深得学生们喜欢。
在画画班,我是几个较勤奋的孩子中的一个。每次来得早,走的迟,好问问题,深得老师们喜欢。这样,画的画也就最多,画材消费也就最快。为了节约开支,我只得尽可能的节约着用,速写纸画了正面画背面,水粉色用色尽可能地少,够用就行。由于挤的颜色少,老师在改我的画时,常常会说,“孩子,你的颜色挤得太少,还没调和就用完了,这可怎么改呀?”于是,我就多挤一些颜料出来,看着那一堆堆小山一样多彩的颜料,依次整齐地排列在调色盘里,我的心紧紧地揪在一起;可不要用完了,要不然,又要向年迈的父亲伸手要钱了,要那从水果箱里挤压出来的皱巴巴的血汗钱啊!
那段时间,我很快认识了几个农村来的孩子,并且很快发展成为好朋友。
方正平,汉中来的,圆脸,人较胖,肤色稍黑,说话直来直去,一是一二是二,从不绕弯子。
刘忠宏,礼泉人,颧骨高,眼睛较小,画画爱较劲,好争论个高高低低,人直爽乐观。
学习间隙,我先后受邀到他们租住的高大明亮的房间去参观交流,他们也希望到我住的地方看看,我都一一谢绝了。原因很简单,我不想让我的朋友去那个四壁黝黑,只能容下一张双人床的小空间里去,插不进更多双脚的地方去。更多的一点,也是我的虚荣心在做怪,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位拉着架子车,被别人远远就捏着鼻子喊,误认为是收破烂的城市边沿人。
方正平是第一个带我进学生舞场的人。在那色彩斑斓的世界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现代年轻人,第一次感到了城市夜生活的丰富多彩,在那炫目的流光幻影下,颤抖和跳动着的一个个燃烧的灵魂。而我,一个衣着简陋的农村孩子,那一刻,是多么的麻木和无知,一次次踩踏了人家女孩的脚尖,双手也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一次次硬着头皮想离开,却又盛情难却,只有在那流动的人群中硬撑着,脑门背脊尽是汗,紧张地心像跳到了嗓子眼,真想很快找到地上某个缝儿钻进去。
在学习班,我吃到的第一个苹果是刘忠宏给的,他家有成片的苹果园。礼泉的苹果个大味甜,可以说,那个苹果是我长那么大所品尝到的最好吃的苹果了。为了感受秋收的欢乐,那个秋天,我们一行几个好朋友,一起来到礼泉县刘忠宏的老家,我是第一次看到了那满眼的苹果园,沟沟梁梁,一浪一浪的红通通的苹果,孩子的笑脸似的,那样让我们陶醉其中。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空气中流淌着甜丝丝的果香,辛苦了一年的农人正在收获,我们挽起袖子,很快就参与到这秋收的队伍里,采摘一蓝蓝希望,收藏一筐筐梦想。苹果一个个下树,再分类进筐,最后用长绳掉进数丈深的地窖里,码放整齐了。我们感受了果农的收获之美,每人回来时,又收获了一大包沉甸甸的大苹果。
在那些日子里,除过半天的画画,我大部分时间是趴在竹板床上,背那些枯燥的历史、时政题,反反复复书写着虫子一样的英语单词。有时,我关了房子门,静静地躺在那个黝黑的斗室里,斜斜地注视着窗子外面那一小片天空,白云一团团飘过,小鸟儿叽叽喳喳在高大的楼宇中穿飞,各种各样的小商贩高高低低的叫卖声……自由是他们的,而此时的我,真真正正的像一个监狱里的囚徒,笼子里的灵鸟,玻璃缸里的巴西龟,苦苦地守着时光,没有欢笑,没有歌唱,没有鲜花,只有四壁黝黑的墙,满床堆积如山一样的高考复习资料。
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傍晚,父亲拉着水果车回来,看着年迈的父亲大口大口地吃着自己做的甜米饭,一遍遍地数着一堆皱巴巴的票子,讲着一天在外面遇到的奇闻趣事,我的耳朵伸得老长老长,生怕漏掉了任何一个小小的细节。
房东是一个肥胖的老女人,走起路来一身肉褶子,肉都都的圆脸上,一双小眼珠咕噜噜地转来转去,嗓门较高,瓮声瓮气的,好说是是非非的话,只要一提自己的几个子女,就有一肚子的话讲不完,这个长来那个短,直到听得你心乏了腿困了,上眼皮直挨下眼皮,她才惺惺停下来,没有尽兴地摇头离去。
房东的老伴是个干瘦的老人,身体硬朗,年轻时学得一手好拳脚。每天晚饭后,他都会来到我们的灶房门口,扶门谈天,你给他板凳都不坐。我最喜欢听他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他练锁子石,能单手将七八十斤的锁子石绕过头顶轮上百圈。看电影走夜路,一走就是几十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有时还要经过几个大坟场,他一路吼着秦腔,手里一杆槐木棍,天不怕地不怕,凭他学的十几套拳路,一人对付十来个小生不成问题。直到现在,近七十岁的人了,没得过什么大病,还能单手连劈数十块砖。老人的传奇经历,让我非常羡慕,以至于之后的几天,我也偷偷地在床上练起俯卧撑来,我多想有老人那一身好功夫啊!
夜幕降临,看着窗外天空上的繁星,我久久不能入眠。父亲睡得真香,一浪浪地打着鼾声,看着月光下老父亲那瘦削的脸,深陷的眼窝,花白的胡子头发,我的心开始滴血。本该是安享晚年的老人啊,为了我的学业,不得不将自己套在车辕里,老牛一样,从早到晚,拉拽着沉甸甸的岁月。我一遍遍地发誓,并狠下心来,不考上美院誓不回头,我要圆自己的梦,更是要安抚老父亲那一颗操劳一辈子的心。
一九九四年八月,我先后收到两个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一个是西安美院,一个是宝鸡文理学院。一九九四年九月,我如愿以偿地坐进西安美院油画系壁画专业的教室里。
这篇文章好看吗?
是 否
已有 人觉得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