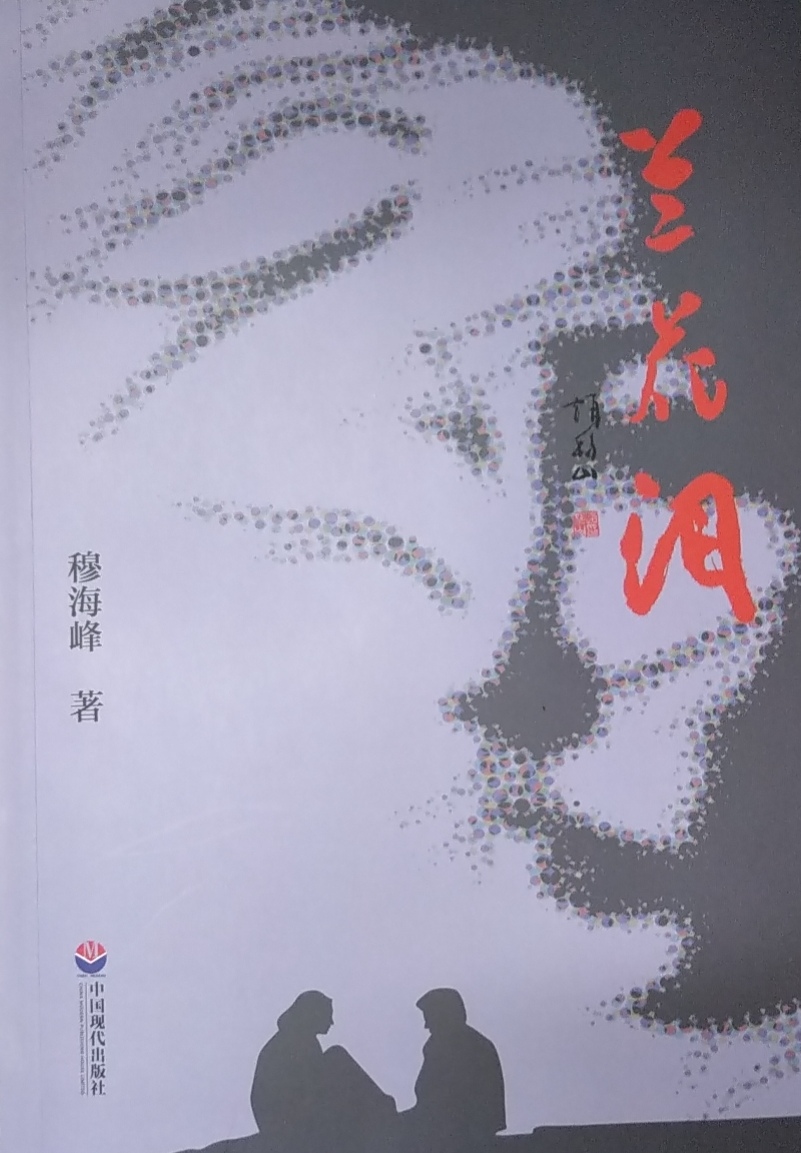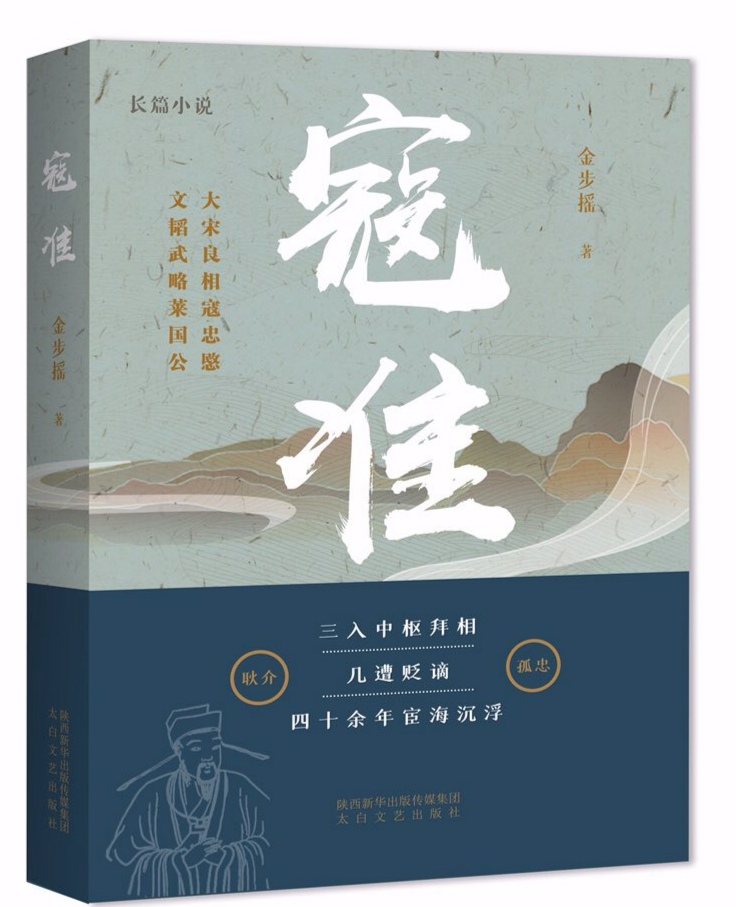羽鹏芳
也许是信天游的功劳,把陕北特有的“那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梁”,“风沙茫茫满山谷”,根植在人们心中,因此沟壑纵横,山峁起伏连绵,土地裸露,尘沙弥漫......成了陕北的名片。殊不知,在陕北南部的黄河岸边还有一个,层峦叠嶂,山势巍峨,嶒崚插天,森林茂密,流水清涟,气候温润,一副南国风光的景象的地方,这就是宜川县的土石山区,被称作是陕北“后花园”的地方。这里容纳了宜川海拔最低点388米和最高点1715米的湍急过渡,涌现出了著名的蟒头山,八狼山,盘古山一些列杰出,藏匿着濒临灭绝动物褐马鸡、林麝等精灵,出现过随同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一块打天下的英雄罗霸王,是个颇具神秘、令人遐想的地方,也就是这个地方竟然还保存着,被北京摄影家成为“陕北最后的石板房村”的世外桃源——窑科村。这还得从年初的北京摄影家采风说起。
大年初一的鞭炮爆裂起噼噼啪啪、轰轰烈烈的氛围尚未消退,摄影协会的郭主席就打来电话,几句祝福词一完,就嗫嚅地说:北京摄影协会几位朋友明天,也就是初二要来宜川拍照,考虑到我是外地人,亲戚少,时间充足,希望能陪他们几天。既然领导发话了,去就去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再者,尽管自己对光影艺术缺乏灵感,悟性愚钝,但能跟陪高手采风,认识几位朋友,也是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
慵懒的阳光趁着假日悠闲散漫起来,直到十点多才爬上南山的塔尖,宝塔一撑腰就立即散发出耀眼的光芒,直射的我难以睁开朦胧的睡眼。突然想到今天远方客人要来,就有电波告知他们十点已经出发。我想北京——宜川,千里迢迢,关山阻隔,加上这冰天雪地,凛冽寒风,谈何容易。悠而闲之地洗漱、吃饭、喝茶,和子女们拉着家常,不知不觉已经送走了半天的时光。刚放下碗筷,就收到他们下午四点可到宜川的信息,我为之震惊,
看来在今天那种神行太保式的“日行千里”、“朝发夕至”已不再是神话的传奇。
饭桌上几句简单的寒暄后,为首的摄影家李光明老师就切入正题:千里迢迢赶来,就是想趁过年拍点民俗的东西,你们看看应该去哪里?路线给咱划计划计。
我突然想起了朋友说过的事:那年为了逃債而在一个名叫磊(当地人念luo)义沟后的一个村子住过,并说那个村子全是石板房子,生活原始,除过“公家”催粮要款,很少有人去。信口就说去看石头房子吧,那里也许保留一份宁静与自然。
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让同行的两位北京女士惊讶,惶恐、昏眩、呕吐,但仍然为起伏连绵的莽莽群山,千摺百皱的姿态而嗟叹、那份少女特有的好奇与天真被激发,一会要看窑洞,一会要听松涛,一会又说看见褐马鸡(这是我们行前给介绍的)......。总是叽叽喳喳不停,给旅途带来了不少轻松与愉快。
走过两条沟翻过两架山,驶出20里阴凉沟,终于到了磊义沟。沟很窄,两边对峙、高耸的山峰犬牙交错,路就在这夹缝中盘旋,真让人有一种“山重水覆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渐渐天空阴郁起来,给本来就沧桑的山色增添了几份沉闷,沟很深,时宽时窄,道路蜿蜒坎坷,夹道的野生灌木张扬无忌,对来客表现出了过多的热情,伸出横斜的枝梢把汽车挂的唰唰作响,高悬枝头的喜鹊,忘记了啄残留的柿子,嘎嘎几声欢迎词后,就匆匆飞走,也许是忙着回去给主人报信去了。
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行驶十几公里,经过一个耸立在道旁的山峰后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石板房,一个叫窑科的小山村,也是这条大沟里最后一个村子。
村子坐落在一个像巨人伸展出一只脚的山角小土峁上,两旁山势崱屴,森林茂密,一小河条蜿蜒而过,冰封的河面只有芦苇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沟道尚算宽阔平坦,几只山羊悠闲地觅食,嬉戏。河对面有几座古朴的石板房,一条小路绕道峁后,一切都显得安静,悠闲,真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
一顶羊肚子手巾缠头,躬腰驼背,老棉袄泛白,手柱拐杖的老头蹒跚着走来,看见我们就笑眯眯地说:那哒(听到的音符,不知对应的汉字,应该是山里人的打招呼语言),你们来了,过年好!我不禁为之惊奇:这些几乎是隐居在深山的人们,竟然对外人没有一点的陌生感,倒充满了不设防的亲近感。
北京的老李曾是那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中的一员,插队的地方就在宜川的云岩镇,回城后当了新华社的摄影记者,但对这方热土情有独钟,对宜川人倍感亲近,连忙用略显生疏的宜川话对老头打招呼,发烟。老头也不客气,笑眯眯地接过去,一根接一根抽着抽,口里轻轻吐着烟圈,本来皱摺的面孔显得模糊,似乎沉浸在一种幸福的遐想中,令人感到像这座大山一样显得厚重,颇费琢磨。
转弯处有一棵合抱粗的大梨树,树冠巨大,以迎客松的姿态横亘过小路,和站在树下冒着烟雾的老头、背后连绵免得山峰,萧瑟的疏林,形成了一道美妙的风景,给摄影家留下了无数的底片和想象。
真佩服古人的才智!这样一个小山凹被安排的合情合理,既背风向阳,又十分隐秘。村庄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层三组,第一、二层分别顺山势各由五六个由石墙垒起的院落组成一组,层与层之间是干石垒砌的高硷,第三组也以同样的结构回折靠山。就在这石头硷畔上还生长着粗大的中槐和其它树木。墙壁上一副“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标示了时代节拍的缓慢。一位颇有几分诗情的女士感叹:村靠山,水绕村,树木掩遮,石屋点缀,多么美妙的一副山水画呀!
由于正值新年,一份休闲和欢乐的气氛在这里迥然荡漾,石墙上的大红对联,高挂在门口树上的大红灯笼,捂着耳朵在硷畔上燃放着炮竹的孩子,穿戴整齐,悠闲的踱步串门的男女,荡漾的现代流行音乐,门口停放着的一辆小面包车........把过年的喜气装点的浓浓烈烈。热情好客的山里人,在吉庆的烘托下显得更加热情,看到我们一行到来,纷纷上前问好,祝福,邀请大家进屋暖和,喝水。但那些痴迷的摄影人,早被这颇具魅力的景象陶醉了,忙着把一道道风景,一棵棵古树、一座座石头房子,一个个憨厚的村民,一个个顽皮的孩子的形象囊括在相机里。
看到大家如此痴迷,一位村民主动带我们来到村子的窑背上。这时天上突然飘起了轻盈的雪花,迷茫的雾气给这偏僻的村庄披上了神秘色彩。放眼望去,沟道层层梯田在两山的裹挟下渐渐朦胧,地里堆放的玉米干,像一个个披着白色风衣的山里人默然坚守。俯视千姿百态的石墙、石瓦、石径和石具,经年的风雨,把石板冲洗得一尘不染,泛着青白,叙述沧桑。院墙用石头垒砌,无灰土和水泥铺垫填缝,但每块石板就像一块块墙砖一样,镶嵌得天衣无缝。屋顶也是用青一色的薄石板苫盖的,远远望去,就像一层层鱼鳞排列在石板房上,显得整齐而有韵律。院内的厨房、猪圈、鸡窝、厕所也都是用石板或石块砌垒的,院落的桌、凳、灶、碾、磨、槽等也都是用石头凿的。一条条弯曲狭窄的小道连接着每一户门口,显得自然、质朴、纯真。石屋造烟,石径悠长,石墙夹着石径,石径缀着石房,连成的是一个石的世界。更能感觉到原生态石板房的魅力和石板房的自然美。在这里石板房依然依然风韵犹存,继续承载着千百年的梦想,依然发挥着它的实用功能。
大家摄兴尚未消减时,就听到一位老大爷在下边喊话:唉!你们下来,暖和暖和,我把水烧开了,茶也泡上了,不喝就辣(凉)了。这样的热情谁会推却呢?
山里人没有外面世界那么多的猜忌,警觉和安全防范意识,老大爷的家竟然干脆连大门都没有,对联就直接粘贴在外墙上。可能是山里地皮短缺的原因,两座相对各三四间的石板房构成院子显得窄狭,阴暗潮湿,尽管是隆冬但那些用石板铺成的地面上依然可以看到苔藓墨绿色的身影。
门口一个用泥巴做成的土炉子上翻滚着甘洌的山泉的清香,古老的木板门旁一副大红对联上写着“勤劳人家春常在,和谐社会幸福多”感到特别醒目,与这残破的石房子形成鲜明的对比,门口涌出了阵阵扑鼻的茶香。也可能是雪的炫目进门后却感到一片黑暗。屋子也很窄小,算是一明一暗那种,进门这间算是厨房,隔到小门那间算是卧室。卧室的多一半几乎由土炕占领,靠窗的地方有个老掉牙的木桌,两旁是箱笼和堆放着的杂物,一个17寸的彩色电视机突兀在这凌乱,阴暗的房间,显示出了几分现代化的气息。
一路颠簸,忙于拍摄忘记了口渴的北京客人,无忌这里的脏乱,,大口大口地喝着这“山里茶”,拉些家常话,俨然像常客一样的自如惬意。
慢慢我眼睛适应了环境,看清楚了这间厨房和摆设:不知多少年的烟熏火燎,房梁,墙壁已经黝黑的流油,加上天气阴暗,难怪一进门啥也看不清。靠炕的隔墙下是一个土灶台,灶台上摆放着石臼,瓦罐,瓦盆,靠山墙摆放着厚重的案板,水缸,还有一个荆条编制的粮食屯子,零散夹杂在这些中间的什物有,搪瓷盆,塑料盆,塑料袋等等,简直是一个古今农村家用什物的展馆。
我想起《桃花源记》中:“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便好奇问大爷:你们是这的老住户吗?老人说: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老爷手里就到这,现在全村有七十多口人,年轻人大多出门打工了,就剩些老人孩子。我想,四代人,最起码有百年历史,百年前正是中国积贫积弱,战乱不断的年代,也许他们的祖辈是怀揣着避乱、能填饱肚子的基本需求和理想才避乱隐居于此。那么,他这些朴素的愿望在过去和今天实现得如何?老人没有一句抱怨,只是好奇地问这问那,关心着外边的世界。也许大爷脑门上奏摺里那些隐藏着数不清的悲喜故事已经随着年轮淡化,烟雾飘出的只有满足的笑语,眸子里流露出的似乎只有幸福。山里人就是这么朴实。
一个身穿红花棉袄,头上扎两个羊角小辫子,碰碰跳跳来到我们面前:叔叔、叔叔,给我照张像吧,她那种天真无邪,纯真,祈求的眼神把大家都都笑了。女孩一点也不怯生,站在院子里的玉米桩前,摆出各种滑稽、可爱的姿势让我们给她拍照,一时气氛活跃,笑语不断,热闹非凡,把新年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李老师是摄影大家,突然来了灵感,用鱼眼镜头把这个小姑娘拍成了拖曳彩云的仙女一般。
雪越下越大,渐渐地覆盖了院落,道路,挂满了树枝。当我们要走时,主人也说:那就不留你们吃饭了,赶紧走,路上可要小心,特别是下将军台那个陡坡是一定要慢点。
将军台!这个地方在宜川也算是小有名气,来时却因寻找石板房而忽略。
艰难地下了村民说的那道坡后,停车仰望,只见路旁不远一个突兀耸起的独立山头,酷像一位身材高大,身披铠甲,头戴铁盔,神态专注,表情肃穆,仰面远眺的古代将军造型屹立在那里仰天长啸。像是这个村庄守护神,尽职尽责地警视着一切,难怪这里的人们能有那么长久的安宁与“幸福”;也许他是明崇祯年间带领贫困农民造反的领袖---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罗霸王的化身,在作“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仰天长叹。总之,我感觉到它是怀着某种向往在长久地恪守着期盼。
兴致骤起,我想到《桃花源记》中有:“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我便频频回眸想牢牢记住这里,但见山舞银蛇,白雪莽莽,只有两道车恨在不断拉长。
回家后我久久不能平静,翻阅有关石板房的文章,看到的多是:石板房部落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但留了人们原始的生活见证、原生态文化、建筑文化遗产等的等等。好像石板房已经是一个渐远的记忆,殊不知在这里她虽然苍老,斑驳,但依然活生生地养育着一代又一代人。
回味当时我问村民有啥想法时,他们说,现在政策好,吃穿没问题,算是幸福,就是可能政府忘记了这里,道路一直不好走。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无怨无悔,无尤无怨地铺垫在社会的底层。
山里的人对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外面人也多了份回归自然充满了冲动,这种互动中的人们,像大地五线谱的音符在跳跃中律动,寻找生命的定格。而这片依然保存着原始形象的村落,未来是开发?是搬迁?还是......位置到底应该定格在哪里?
这篇文章好看吗?
是 否
已有 人觉得挺不错!
最新文章
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