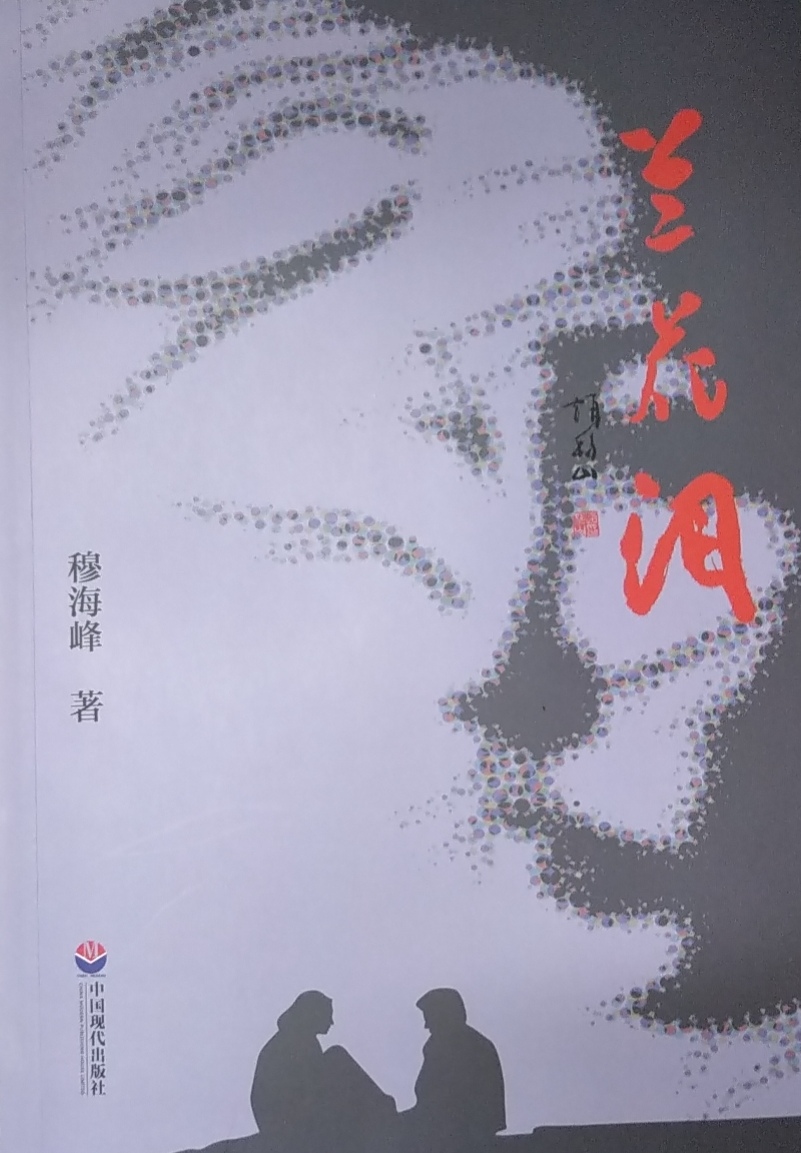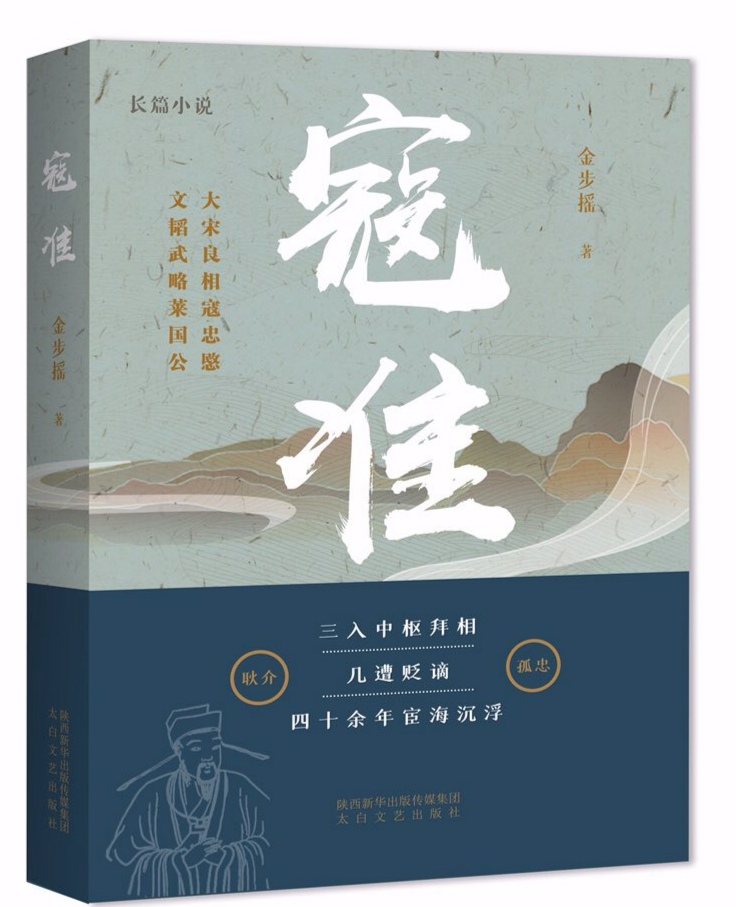周向峰
早晨8点钟,王晓枫拎着背包,走进了后稷乡街道中间平时看起来一座不显眼的关中民院,心里觉得万分诧异。这难道就是我要上班的地方,心里一下子灰了一半截。

这是一座典型的关中民屋,在院落墙外悬挂着一张“后稷工商行政管理所”的吊牌,院落左侧是一个偏房,一看便知是农村的厨房。里间上房是一栋两层小楼。走进一楼是一个四十多平米的大客厅,里面套了三间小屋。
王晓枫迟疑地走了进去,只见客厅东面沙发上一个秃顶的男子正襟危坐,双手合什,微闭双眼,嘴里念念有词。客厅南面靠窗户处摆着三张办公桌,一个带着石头眼镜的中年男子端了一杯茶,跷着二郎腿,斜眼看了晓枫一眼,冷冷地说:“你找谁?”
“你好,我是从财校新毕业的,县局人教股让我到所里报到,这是我的介绍信”,说着,晓枫毕恭毕敬地双手呈上介绍信。
“老路,新分来的学生,”戴眼镜的头向里间的房子吼道。
这时从东面套间走出一个满脸胡子的人,左裤腿挽着,趿拉着鞋,嘴里叼着一根烟,“噢,你就是王晓枫,人教股昨天打了一个电话,说给咱所里分配一个学生,欢迎,欢迎”。路康平随即问了晓枫的一些情况,然后扭头问戴眼镜的白争权:“老黑,你看给晓帆咋安排呀!”
戴着墨镜的白争权,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茶,淡淡地说:“你是所长,你安排吧。”路康平嘿嘿笑了几声,带着商量的口气说:“要不将一楼东面的房子收拾收拾,让晓枫住下!”
白争权不容置否坚定地说:“也好,刚来,先让娃熟悉一下情况。”
王晓枫突然想起了什么,急忙从背包里掏出一包软芙蓉王,拙手拙脚地拆开,一根一根向路康明、白争权、严得利三人散发,王晓枫向坐在沙发上置若罔闻、正在专注地看着书的人递烟时,那人闷头不语,仿佛置若桃花源中的闲云孤鹤、世外高人。
“老严,娃给你发烟呢。”
看书的人才缓缓抬起头,笑了笑:“不抽,不抽”。晓枫偷眼一看,看见那人读的竟是一本《圣经》。
闲聊了一会,晓枫才知道,这后稷工商所里只有四个人。所长路康明,会计严得利,干事白争权,加上他这个新来的大学生-王晓枫,负责着后稷乡的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
后稷乡东邻杨凌国家农业示范区,是农业始祖后稷的故里。姜塬村、揉谷乡这些与农业之神的相关的地名至今还烙印着古老文明的印记。传说5000年前,这里是炎帝的部落,记载了黄河流域文明最兴盛的辉煌,后稷稼穑,躬耕乡梓,农业经济的发达,使其成为华夏最富饶的部落,强大的经济基础为氏族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保障,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纵横驰骋,最终促使炎黄部落结盟,一统华夏,奠定了五千年的悠久历史。
路康平:“老严,姜塬村今天有会,要不咱趁早走,到庙上看一下。”说着,路康平等人一行收拾停当,来到一个破旧的三轮摩托车前,墨绿色的车身衬托着后兜上红色的背椅显得特别刺眼。路康平带上手套,左脚在启动器上使劲踏了好半天,终于发动机像拖拉机似的嘟嘟嘟吼叫了起来。王晓枫好奇地说:“这背椅怎么是个红色的?”白争权心直口快,“哎,老严,你看你把这个背椅怎么弄了个红色的,不是说你,颜色劣的很,咱行政单位,主色调是黑,或深蓝,要搭配开才行!”
“人家木器厂只有红色,再说咱工商所让人家义务做,不掏一分钱,还弹嫌枣没糊糊!红色喜庆,黑色挽帐是黑色,多丧气。” 严得利怨气地说。
“走走走,时间不早了,赶紧走”!说着路康平骑在摩托车上,白争权当仁不让坐在车兜里,严得利则跨骑在摩托车的后面。王晓枫愣住了,不知道自己该坐在哪,路康平说:“晓枫,你坐在备车袋上,抓紧。”
王晓枫坐在三轮车后箱的车袋上,双手紧紧抓住靠椅,摩托车鸣了一下号,风驰电掣地驶出了后稷工商所。
沿着泾渭渠,去姜塬庙会赶会的人熙熙攘攘,三轮车、自行车、汽车、架子车蜂拥在西宝中线上,路康平骑的摩托车不停地鸣着号,飞速向前冲去,在前面拐角处的绛帐十字路口,有一辆警车正在疏散来往的车流,晓枫心里胆怯,“路所长,要不我下来走吧。”
“没事,是交警队老邓,别的车他挡,咱工商所的车九是通行证。”果然在路口,路康平骑着车,在警车面前鸣了一声长号,白争权坐在车箱里,像首长阅兵似的摇了一下手,那两个交警笑了笑,点点头示意过去。
姜塬,是古代农业之神后稷的母亲。据说姜塬圣母在年轻时,有一次在渭水边漂洗衣服,看见一个巨大的脚印,便好奇地踩了上去,谁知因此而身怀六甲,生下了农业之神后稷。这里位于八百里秦川西部,地势平坦,年年经渭水冲刷洗礼,土地肥沃,后稷成人后,成为部落首领,带领部落人在农田里精耕细作,春耘秋获,很快使农耕技术传扬广大,原来四处迁徙的人们慢慢在此定居,四方部落纷纷归顺,成为华夏大地的农耕文明中心,并迅速向各地传播,使华夏子孙饱肚腹,知荣辱,农耕文化盛极一时,姜塬圣母后稷故里的美名也沿袭至今。无从考据的这个姜塬村落的庙会流传了多少年,每年都吸引着甘肃、河南、宁夏及周边县区永寿、周至、户县、武功、岐山、凤翔、陈仓等省内外十余县姜塬的信众,长途跋涉,顶礼膜拜。据老人们说,姜塬圣母灵验了得,在庙会上多年不孕农村小媳妇在小脚婆婆的带领下虔诚求愿及还愿的人络绎不绝。姜塬圣母塑像前披着一个又一个红被面,庙门前还愿的鞭炮声噼噼啪啪地响个不停。
二十分钟后,后稷工商所的车驶进姜塬村时,狭长的村路两边早已被撵会的人堵了个结实。蜂拥的个体户们霎时像欢迎贵宾似的呼喊了起来,埋怨声、期盼声交集在一起。一些熟悉的经营者热情地打着招呼:“路所长,啥时安排摊位呢?”
“急啥呢?等烤干歇黄了再安排不成”,路康平边骑车边笑着说,好像是一个农民站在丰收的庄稼地里,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情。
“让开,让开,给工商所的车让开路。”一个机灵的工商户喊着,纷扰的人群中霎时裂开了一个缝,等路康平的摩托车缓缓地驶过去,身后的人群又像潮水般地合拢了,一辆黑色豪华奥迪小汽车拼命的在后面摁喇叭,可是人流却仍然纹丝不动,彷佛陷入了空寂的山谷之中。
姜塬庙在姜塬村的北面,迎对面是一个占地十多亩的广场,广场正中间上面赫然书写“姜塬沃土育生灵,后稷稼穑度苍生”。路康平、白争权、严得利、王晓枫四人在庙中停歇下来,庙上的姜会长迎了上来,看上去有五十多岁,热情地拉住白争权的手说:“所长,你可来了,刚还让人给所里打电话,那些贩子为地方吵个不停”。
白争权嘿嘿地笑一言不发,严得利则皱着眉向旁边扭着头,路康平却习以为常。王晓枫后来才知道,原来白争权在后稷所工作了近十年,人熟关系熟。路康平、严得利两人都是从外所调来不久,加之白争权个性张扬,敢说敢为,路康平则性格内敛,少言少语,一出门就被人误认为是领导。
姜塬庙会据说由杨凌、周至及县境内与姜塬有关的十三方(村)组成。每年庙会由十三方轮流承办。会长姜天福就是姜塬圣母娘家的多少代嫡系后裔。姜塬庙原来占地二十多亩,但近年来庙上香火旺盛,不断向外扩大地盘,经常由于地皮摊位和人发生纠纷。因姜塬庙会属民间自发组织,加之十三方声势巨大,影响甚远,姜塬村委会及镇政府在处理庙上的事时,舆论上处于劣势,在争执中往往败下阵来,村上镇上的领导只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凡庙上的事大多闭只眼睁只眼,躲的远远的。
而平时庙上十三方的人不显山不露水,但只要庙会承办期间,便如雨后春笋般的站出来,一下子直起腰杆,拉开架势,吆五喝六。会长姜天福指令各地信徒到各村讨面讨油,走到谁家门口,这些农村小脚老太婆像拿着上方宝剑似的,在各家门口理直气壮的大喝一声:“给庙上讨面呢!”主人们便慌忙从屋里跑出来,笑嘻嘻地接过面袋,狠狠地从面盆中挖上五六勺面,有些家境富裕的人家或主动打上二三斤菜油,以示忠诚。
信徒们将讨要的面、油醋一一登记在案,用红榜张贴在庙门前,跟会的人和村上的人围站在那儿,一边议论谁家大方,谁家是个啬皮。当事人在众乡亲面前长了脸,一家人都荣耀无比,有的人没有捐或是捐少了点儿,或低头羞愧,回家狠狠地把媳妇数落上一顿,嫌在众人面前丢了人。家里有老人的便气狠狠地赌气不吃饭,嫌对圣母娘娘不忠诚,丢人现眼,家里的媳妇像做错事的孩子,坐在灶房里,一手拉风箱,暗暗啜泣。
在庙会期间,庙里指定全村百十余户安置远自十二方的客人。凡是有接待任务的人家,必定要腾上一两间上好的屋子,安排客人,倒烟沏茶,以显示圣母家乡人的热情好客遗风。
原来姜塬庙会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当做封建迷信予以取缔,但是流落十三方的后人仍然在三月初十这天不约而同赶来叩礼膜拜。为此红卫兵从四十余里外的县城处集结而来,将这些“封建残余”抓起来游行示威,三月初十既是圣母会,又是扫除旧封建的批斗会。十三方的信众偷偷将圣母像藏起来,当红卫兵闯进庙里,企图搜姜塬圣母像时,被愤怒的人群围住,一只黑红有力的臂膀抓住领头的红卫兵头目的胸口:“你个死皮蔫娃,想干啥?”人群中一双双眼睛露出愤怒的火苗,那群红卫兵见事不好,便灰溜溜地走了。一时间,姜塬庙会声名大振,护庙有功人士像大侠一样,名字迅速传遍渭河两岸。
晓枫在一旁偷偷的对路康平说:“路所,这庙会上的人咋对咱工商客气的很?”
路康平嘿嘿笑:“市管会的时候,县革委会召集民兵,多次来取缔封建残余,都不见成效。后来改革开放后,庙会上耍杂技、算命、卖假货的人多了起来。庙上出了几回事,只好请工商所来帮忙。有一年,庙上和工商为收会费,关系弄僵了。后来经县局联系,会费庙上占35%。工商所人扯票,庙上人收钱,这几年关系与庙上才有所缓和。
白争权和姜天福,坐在那商量议论了半天,最后扭头过来,问“老路,你看咋样?”
“好,好,就按老黑说的办,分成两个组,咱一人一本票,老黑和晓枫负责布匹、餐饮。我和老严负责小百货,和杂货。咱人少,先集中把摊位登记起来,最后按分组收费。”。庙上共派了12个毛头小伙子,加上工商所的人,霎时16人的队伍从庙里浩浩荡荡的涌了出来,走在一起,队伍雄伟可观。他们刚走到饮食区,周围的个体户便围了上来。
“老黑,你工商所是干啥吃的?咋还不划摊位,你看捶(打架)打的成啥呢?”
“老黑,我昨晚1点就来了,就是把摊位摆不下,说是在人家门边头,不让我摆,你评评理”。
“这是我地里,我想摆哪就摆哪!”一个摆凉粉的恼冲冲的说。
听到这话,白争权停下了脚步,紧盯着对方:“你说啥话!你地里?天安门广场大的很,你咋不到那摆去呢,都是国家的,今年会上饮食摊位一户30元,谁先交钱给谁安排地方”。
周围的人开始哄哄的一声:“啊,工商所的人太心黑了,原来是15元,现在咋又涨了?不能缴!”
人群中迟迟不见动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闹哄哄地一片,没有反应。这时那个从远乡卖面皮的挤了进来:“来,老黑,给30元,你给我安排一个摊位,我从昨晚来,为找地方和人把捶打遍了,不淘这个气了!”
白争权伸手接过钱,大喝一声:“开票”,只见严得利麻利地掏出行政事业性票本放到黑皮包上:“叫啥名字”,“杨金河”,写好后撕了票,将钱交到庙上的人手里。
老黑手一指,“卖凉粉,把摊位让开。”
卖凉粉的急了,“啥,我为这地方前十几天就让家人占着,就没这点权利了,庙会就在我们村门边头……”。
“你挪不挪,问你一声,不挪了我就动手”。白争权黑着脸,两眼紧盯着对方。
卖凉粉的仍然向周围一群人诉说着理由,白争权向后吼了一声:“来,把东西打折了。”16人顿时围了上去,抬桌子的抬桌子,抬板凳的抬板凳,卖凉粉的一边阻拦,被老黑狠狠地掀了一把,将杨金河的摊位安排了上去。
“下一个,谁要?”周围的个体户看到这情景,立即围了上来,“老黑,把我钱接上,老黑,把我钱接上”,白争权仿佛像个将军大手一挥:“别急,一个一个来。”
白争权接过个体户缴来的钱,随手给庙上的人,念一个名字,严得利飞快地开着票,周围有的个体户急了,没有被老黑接过钱,怨恨地说:“老黑,你看你,咋不认人呢?”白争权一言不发。
有一个熟人乘乱把钱塞到严得利手里,“老严,咱是老关系,给我开票,开票。”严得利见是县城南街的一个老个体户于晓红,随手开了一张票,没想到于晓红拿着票却被白争权推到一边,于晓红喊到:“老黑,你说这是不是你工商所开的票,凭啥给我不安排摊位,你真咯吧共产党的事执着,欺负人呢?”
白争权闹了个大红脸,他扭过头来,气狠狠地说:“老严,怎么个事嘛,来来,你给安排摊位去”。周围三四十个人围在一起,一个庙上来帮会的人说:“这事要一个人来弄呢,不能都接钱”,严得利红着脸一声不发,路康平在旁打着哈哈,“老黑,对咧,就这一次,划摊位,划摊位”。
白争权用手一指,让于晓红摆在刚才已安排的摊位上,那个人却不答应了,“老黑,要讲个先来后到,你把我钱接了,咋能弄这个事嘛”!
白争权急了,“你把票给我,我不收你这个钱呢?”
“凭啥,我钱都交了,为啥不给我安排这个摊位?我又不是没交钱”。那人得理不饶人,不依不饶。
白争权和所里的人觉得理亏,没有人说话。这时路康平走了进去:“兄弟,你声音放慢些,人不知道你还以为你挨刀子呢?”
那人是个“老油条”,拉着路康平说:“路所长,你给我评评理,老黑他办了啥事嘛,把我钱收了,让后面的人把我队掺了”。
“你还撵会不撵会,跟工商所打交道不!甭说了”,路康平说着俯下腰将那人的板凳向后挪了挪,放好,“好好做你生意,甭和人执闲气,咱来日方长,绝对不让你吃亏”。
“看你所长哥把话说到这份上,只不过老黑这事做的不地道,办事要公正才能服人么!”
登记摊位的继续向前行,身后的饮食摊位顺着村路两边的土塬整齐的摆成了一线。这时刚才那个自称在自家门边头的卖凉粉的凑了进来,把钱递给白争权,笑嘻嘻的说:“老黑,你给我划个摊位”。
“你不是说到你门边头么?你看那能摆,到那摆去”。
卖凉粉的满脸赔笑:“你这是让我和人淘气么?做生意不容易,给划个摊位,我这就给你把钱一交”。
老黑面无表情地接过钱,给凉粉安排了摊位。
等庙会上饮食摊位全部划完了,已是上午十点多了,路康平和庙上的人核对钱票,共计1500元,双方在票上签了字,庙上的人便将钱交给了严得利。白争权在旁说:“咱转转吧,到庙会上看看去”,晓枫说:“要不趁热打铁,把布匹和百货都登记了吧?”“早着呢,等抬轿子的过去,再去登记不迟。”
姜塬主庙在村上的北部塬上,据说是姜塬圣母成仙的地方。距离二里外的姜塬村,有一座辅庙,姜塬圣姑娘家所在地。干净的院落里香雾缭绕,一些善男信女虔诚的跪拜,庙前放着一座披红大轿,里面敬着姜塬娘娘。传说每年三月初十成仙的姜塬圣姑要回娘家一次,前三天的三月初八日姜塬村的本家子弟,要到主庙请姜塬圣姑回家。在这几天里,娘家所有家族男女老少,都要到村前的庙里焚香礼拜,祈求圣母安康护佑平安。三月初十正会这天,村子里的本家子弟抬着姜塬神像浩浩荡荡地向姜塬主庙走去。据说每年的这一天,姜塬圣母要离开家,回到天界,难舍难分哭哭泣泣,在这一天也经常感动上仓,甘霖普降,滋润万物,因此,这姜塬庙会又是关中西部最有名的一个祈雨古会。
上午10时整,姜塬村一片熙熙攘攘,一支百名女子锣鼓队锣鼓喧天地拉开了阵势,从辅庙出发,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穿着刺眼的大红袍,头上裹着一个红头巾,生龙活虎地在前面指挥。在塬两岸上,黑压压的坐满了从各地赶来的老腽婆,头上顶着白手帕,小脚裹着一双耀眼的雪白色的袜子,乐呵呵的张着没牙的嘴巴,兴奋处拍着圈坐的腿乐翻了天,成为姜塬庙上最耀眼的风景线。
三十多名小伙子抬着轿,跌跌撞撞地前行,这时从人群中冲进一群小伙子,使劲阻拦轿子前进,挽留圣母娘娘不要走。一群人分成两派。抬的抬,掀的掀,拦的拦,将姜塬圣母轿子忽而向东忽而向西,不时有人跌倒在地上,刺激着崖两边的人群欢呼雀跃,指点着那些跌倒的人中哈哈大笑,而那被撞翻的人在地上爬起来,连身上的土都来不及拍,如斗牛士一样又涌入抬轿人群中,或挤、或拉、或扛、或掀,陷入了一场混战。这是姜塬庙会最精彩、最绚丽、最震撼的篇章,人群的欢呼声、锣鼓声、尖叫声、哄笑声夹杂在一起,声震九天,这是信众们的狂欢节。圣母轿子在信众的簇拥下,步履艰难的向前冲去。由于挽留圣母轿子的一方人多势众,将抬轿子的一方压住向后拖去,立即又有人冲上去加入护送队伍,保护圣母向前走,但是对方势力太强大,轿子仍旧在原地打着转转。往往到最后,庙里的会长不得不出面阻拦:“狗娃,耍个就对了”,阻拦方也见好就收,一伙人又改变立场混入到抬轿方,护送着圣母浩浩荡荡的向主庙行进。
小百货、布匹摊位由于怕被抬轿的踩踏,将货放在土塬两边,等护送圣母轿子的队伍一过,便纷纷拉开架势,摆摊设点。路康平、严得利一组;白争权、王晓枫一组,各领着庙上的六人开始了摊位登记。
白争权,王晓枫走在布匹摊前叫声:“老王,来把费办一下。”
买布匹的老王笑嘻嘻的说:“老黑,咱老熟人,你做啥事都从我头上开刀呢?”
“这没办法,你以为到你南街,谁让你摆第一家,交30块钱。”
“今年怎么又涨了,三天会,你还让我活不活啊?”
“这都是上面规定,没办法,权当给爷庙积德行善,好好交了,坐你生意”。
“老黑,说句心里话,三天会,30块钱,这有点太便蔫(高)了吧!早上4点开车来,好不容易占个地方,再说,姜塬会年年下雨,你又不是不知道,能买几个钱”。
“你县城南街人就难说话的很,没人抬八抬大轿请你来,是你要来的,再说收多收少,又不是交给我,国家就这么个规定,我又啥办法”。
“你不能向县上领导反映一下”。
“哎,咱两磨了半天牙不结啥颗颗,两米是30块,你看你占了多长地方,有五米吧,至少要交70块。看你老熟人的面,让你交一个摊位钱总可以吧。后面事还多着呢,甭叫我在你这打档档,你的钱是钱,别人的钱是纸纸” 。
“老黑……”
白争权说了半天,见对方无动于衷,一下子恼了,“不收你的钱了。”顺手拿了一沓布,交给庙上的人,“走”。
买布老王一下子急了,“老黑,不是不配合你老工作,少点,少点”。
“你不要得寸进迟,让你交30块钱照顾你,你看你占这么大的摊位,是人家的两个,把你照顾了,还不领情,不要了,走”。
“老黑,对了给25,25,做生意不容易”。
“不行,30块钱一分也不能少”。
卖布匹老王掏出25块钱,硬塞给白争权,“咱弟兄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你甭难日了,我南街人啥时把工商所的钱耽搁了!”
白争权接过钱,咧嘴望着他:“老王,再缴3块钱, 28,啥话都不要说了”。
老王哭笑不得:“你这个真共产党员!”极不情愿的从兜里掏出来3元钱,塞到白争权手里。
“对了对了,认得人不吃人的亏,认得事不吃事的亏,我看你能把共产党的事业干一辈子。”
一行人装作没听见,又向下一个摊位走去,这是王晓枫平生第一次参加庙会,见人这么多,头嗡嗡作响,性格本来内向的他,喜欢安静。如今夹在人群中互相拥挤着,心中不由堵得慌,感到一阵眩晕。他机械的拿着笔,将票本放在黑夹包上面,麻木的开着票,心里盼望着赶紧结束。
白争权头上的汗水滴滴答答的流着,和庙会上卖布皮、小百货摊位的个体户一个接一个的唇来舌往,庙上的一伙人在摊前张一句,王一句,为了不影响生意,会费在艰难中收取。白争权在人群中边挤边回头对晓枫说:“哎,这活不好干,尽得罪人,吃力不讨好”。
时间过的很快,转眼已到十一点了。这时两组的人汇集在一起,聚集到主庙上的一间偏房,议论起收费时遇到的见闻。白争权坐在椅子上,边喝茶边说:“康平,你让老严放快些,收拾收拾咱赶紧回。
严得利将各组分发的票收了回来,一张一张的相加,一组1472元;二组869元,共计2341元。这时庙里的一个人插了一嘴,不是还有早上统一登记的1500元。
霎时房子里的人都盯着严得利,气氛凝固了起来。严得利不紧不慢的说:“我还没算完嘛,这只不过是分组的钱”。
房子里静俏俏地,杳无声息,唯有老严的算盘珠子辟辟作响。只听见珠子像雨点一样时而急速,时而舒缓,像久旱的春雨落在大地上欢快的歌唱。随着严得利的右手将最后一个珠子“啪”的提起。“行政事业票是2982元,定额零星票是859元,共计3841元,庙上按规定35%提是1043.7元”。
这时有人说话:“不对呀,按35%提咋差这么少?”
路康平笑着说:“咱庙上的执事都清楚,手撕的1元,2元,5元是定额票,全部都要缴财政。提成算帐是手开的票,这政策是县局市场股和庙上早几年就说好的,没有啥给攒头”。
“老路,庙上这事你也知道,能维持下来不容易,花费大,全靠收些会费支撑。这每年还要请戏,念经。今年庙上就没敢请咸阳戏,光戏钱要4000多元,我们请的甘肃礼县剧团,好说歹说,才压到了2800元。这点钱还还不够提达钱。
“老姜,国家这事不好办,撕一份票要见一份钱,只有这大票县局才给政策,要不然给财政上没法交差。咱姜塬庙情况特殊,县局才开这口子。你甭难为兄弟了,要不等会后咱一起到我县局市场股说一说,看政策有啥变化”。说着,路康平掏出烟来,向房子里的人散了一圈。
“姜会长,那年我局市场股来人,将庙会上松树以北的白菜心心全部让给咱庙上了,我看了看,今年庙上光这些摊位至少要收3000多吧!”不知何时,白争权戴了一副石头墨镜,气势逼人。
“哎,抢人去呀!咱庙上的人收费,做生意的都不缴,人家只认你工商的人”。
“你要让我收,非收他3000元,你看光饮食摊位至少80多户,一户按30元,还不包括两个马舞团,买成衣的。
“够了,老姜,别哭穷了,这两年国家还有这个政策,支持庙上的事,遇上那几年就没有这么好的事了。老路,咱长期和老姜打交道,给凑个整数按1100元接了吧!”白争权一锤定音。
房子里的气氛顿时松弛下来,响起了一阵笑声,严得利数了1100元,让老姜打了个收条。
姜会长边打条子边说:“咱这庙会神的很,在文化大革命那几年被取缔,远远近近的人都偷着来烧香。革委会每年组织各乡镇民兵来取缔,开现场会。台子都搭起来了,没想到每年都让一场大雨叫冲得七零八乱。我们这庙上共十三方,有西河、青龙、昝家、东官,还有杨凌、太白的;一年由一方主事,其余十二方配合。幸亏大家心齐,才把这庙上香火延续到今……”
“行了,走吧?庙上还有一大摊子事,后两天会费就由庙上收吧,我们也不来了。有啥事咱保持联系”。路康平、白争权、严得利、王晓枫一行人相继与屋子里的人握手寒暄,夹着包包走出了庙门。
姜塬主庙位于一处高崖边,两岸崖谷耸然对峙,下面流淌着一条潺潺的漆星河,从崖底绵延穿过。偌大的广场中央是一座戏台,两边的高音喇叭回旋着演员们激亢的秦韵。台子下面是一群全神贯注的六七十多岁的忠实戏迷。老太婆头上戴着青花手帕,裹着小脚,坐在儿孙们拉的架子车上,一群老汉鼻梁上挂着一副石头镜,柱着拐杖,围坐在一起谈论舞台上戏的情节。
距离戏台东面二百多米远,搭起了一座蒙古包式的歌舞团。一个操着河南普通话的破嗓音在扩音喇叭上大声吆喝:“各位观众,雄风歌舞台即将盛情上演,这里有辣妹表演,刺激火爆,有艳舞女郎激情四射,每位5元,每位5元,快来买票,还有10分钟即将上演……”旁边两个搔眉弄首的年青女郎,揭起歌舞团帐篷一角,像煽风一样,拉开又合上,里面露出四五个三点式的女子在台子中间扭过来扭过去。招引着许多年轻人挤着往进看,却被歌舞团把门的人挡住:“买票啦,买票啦,每位5元,每位5元,这里有辣妹靓姐,大胆裸露开放表演,让你一次过个瘾,让你一次看个够”。
一个农村妇女往里瞟了一眼,迅疾捂住眼睛,往地上狠狠的唾了一口,骂道:“谁家女子丢地卖害,跑这来丧德来。”十多个愣头青的小伙不愿买票,硬往进闯,与歌舞台的人吵吵嚷嚷起来。
严得利和王晓枫一起,在人流中挤着向姜塬村口走去。早晨起来安排的摊位,依次按小百货区、布匹区、饮食区在大路两边陈列,路中间的跟庙会的人在三里路像湍急的河流一样淌动着。好不容易挤到村姜塬,王晓枫问严得利:“老严,怎么咱把一大片划给了庙上让收费”。
“姜塬庙这事复杂,原来因为一直被取缔,庙上的事乡上、村上都管不上,咱工商是一家,税务是一家。可以说敌我顽多方交错,情势复杂。庙上为摊位划分经常打架,个体户不认他们,他们靠咱工商才能收点费。一度时期,咱工商为收费与人发生了争执,庙上的人气了漫,和咱工商打了起来,被认家追了半天。后来,经县局市场股协调,将庙前300米地方摊位让庙上收。这两年关系有所缓和,至于县上其他部门,包括镇上村上都插不进来……”。
不知不觉已到了村口,这时严得利突然被人撞了一下,他侧身一看,发现自己和晓枫被五六个小伙围了起来。
“你是工商的?”为首的一个长毛小伙斜着眼瞪着严得利。
“啥事?……”严得利心里一陡。
“牛皮怂呢?你跑到庙上摆啥威风呢?”说着,顺手掀了严得利一把,把严得利推进了个趔趄。
王晓枫见状,扶住严得利,“你想干啥呢?”
“打你这些狗日的”。
王晓枫身上挨了一拳,他随手挡了挡,顿时这伙人的拳头像雨点一样踢在严得利和王晓枫的头上身上。王晓枫拼命的挣扎反抗,突出重围。一些人后面紧跟不舍,不知什么时候那伙人手里还提着一把菜刀。可是严得利却没幸运,他被打翻在地,爬起来准备往回跑,却被打红眼的恶徒追上,在腿上砍了一刀,躺在地上痛苦的呻吟着。
晓枫跑到村前面的一堆石子前,抓起石头向追着的人扔去。追着的人被迫停下来,躲避着飞来的石子。
那伙人也从地上捡起土块石头,向王晓枫扔去。王晓枫边打边跑,引起周围一阵骚乱。混乱中王晓枫跑到一个饮食摊位上,顺手夺过一把菜刀,这时感觉到头上的血和鼻血在他脸上交织在一起,滴答滴答的淌着,他全然不顾,双手举着菜刀,疯了似的像那伙人冲去,乱砍乱舞。这时庙上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那些人见势不妙,慌忙四散而逃。等晓枫看到路康平、白争权慌张的身影时,眼前一晃,跌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当王晓枫醒来时,见到自己躺在白色的床单,洁白的屋顶,父亲、母亲、姐姐围坐在一起。当母亲悄悄的带着哭腔喊道“枫儿,醒来了,醒来了”。晓枫裂开嘴,想笑但头却干裂的痛了起来。
姐姐焦切的问:“晓枫,怎么样?”
“没事”
母亲突然哇的大哭起来,指着王中权说:“要是晓枫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没完?”
王中权一言不发尴尬的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妈,别这样,这是医院。病房有人呢?”
母亲压抑着嗓子,无声的抽泣起来。
王中权俯下身子,问晓枫:“没事吧?”
姐姐埋怨的问:“你工商是咋回事?才第一天上班,就和人打架?”
“不是打架!我刚收完费,准备往回走,一伙人二话不说,就打了起来”。
“你把事认那么真干啥?能收就收,收不下就对了么?把人都得罪了,欺负老百姓干啥呀”。
“哎,没办法给你说,我们这是工作。我啥事都没做?”晓枫急躁的训斥姐姐。
“不说了,不说了,晓丹”,母亲劝止着姐姐。
“只有晓枫没事就好,医生刚才说,只是外伤”。
“就是,听说他们工商所那个人可惨啊,腿上挨了两刀,流了好多血,要不是抢救及时……”。
晓枫询问了事情的经过,才知道严得利由于腿上流血过多,现在还在抢救。想起这两天发生的情景,他觉得恍恍惚惚地像做梦一样。刚参加工作时,想着工作就是像检察院那样,早上8时上班,按时上下班、坐在办公室里,文静的在电脑上打文件、写材料;或是像姐姐做教师一样,安安静静慢声慢语的上课。可谁想到,自己参加的工作,岗位就是在市场,整天吵吵闹闹的。一天接触的人,竟比自己一年接触的人都要多。
这时耳边响起母亲埋怨声:“你说工商有多好?咋为收费和人打起架了,还动刀子,这单位咋是这么个……”。
这两天路康平头比斗还要大,单位两个人在医院。后稷工商所成了全县的舆论中心,都说工商所为收费让人砍了。不少人说:“你看工商把人逼成啥,老百姓挣两个钱不容易”?局长好几次把他训了个狗血喷头,听说刚分来的晓枫还是检察长的儿子,才上班第一天就出了这个事。原来他还指望这个交流会多收点钱,把上半年任务完成,可谁知出下这事,甭说任务,一切都泡汤了。路康平苦恼的抱起了头,觉得像乱麻一样。
这时白争权火急火燎的掀门进来,“老路,打听清楚了。
刚和派出所杜所长和姜塬村上几个熟人打听,是塬下前进村几个包工头的娃,和杨凌砍刀帮的两个人,一共七个人”。
“咱又没惹这些黑道?”
“是这样,去年前进村会上,税务所徐宁让有个亲戚买成衣,我们收费的时候,他托人说情,咱工商没有认,就提了两件衣服,徐宁让认为是给他没面子,那个卖成衣的也不省事就跟黑道的那帮人说了。至于包工头的娃,那是跟在后面瞎起哄”。
路康平站了起来,“走,咱到派出所去,让把人先抓起来”。
白争权望了他一眼,“康平,坐下,坐下。事没这么简单。你到派出所干啥去呀!前进村那五个娃他爸都是包工头,在市上、县上吃的开。发生这么大个事,人家早把窝子都迷了。我也是听人私下说,没有证据,摆不到桌面上来”。
“老黑,你看这事咋办呀?你可是个老姜塬了,这两天,领导一打电话里训,我都害怕接局里的电话了”。
“听人说,工商局常明宽局长和县上的人说的不好了。有人说工商没有依法行政,工作方式粗暴简单。常局长讲收管理费,国家有法定依据。《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集贸市场管理办法》、《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上面有明文规定。工商收的费实行收支两条线,全部上缴。主要工商是窗口单位,和群众打交道,稍微收点钱影响大。财政、物价、审计把这点钱盯的死,年年检查、审计,有啥出入?这事不知道咋结歇?麻烦的很!”
转眼间严得利已在医院住了三个月。这天晓枫和路康平、白争权去医院看严得利,老严一见人,就痛哭流涕不说话。
路康平安慰道:老严,想开点。县上快对姜塬会上的事要做处理。这后面还牵扯到好多人,迟迟不结案。检察长王中权多次询问:“都两个月了,对刑事伤人案公安局咋还不立案?”有人说:“平时检察院办案都推诿扯皮,轮到你儿子身上才急了。”为此检察院和工商局多次反映,听说县上决定对背后怂恿对抗工商执法的税务人员撤职,派出所长未及时出警,侦办不及时,被调离工作单位。最近还要开公判大会,这下好了,这事就算过去了。主会保佑你的,让那些恶人遭到报应,咱们是依法行政,是积德行善……。
路康平等人安慰了一阵严得利,让他安心养病。走出病房时,耀眼的太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突然传来布谷鸟的叫声,不知谁说了声:麦快黄了!路康平的头猛然嗡嗡作响:“呀!今年任务可咋办吗?”
这篇文章好看吗?
是 否
已有 人觉得挺不错!
最新文章
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