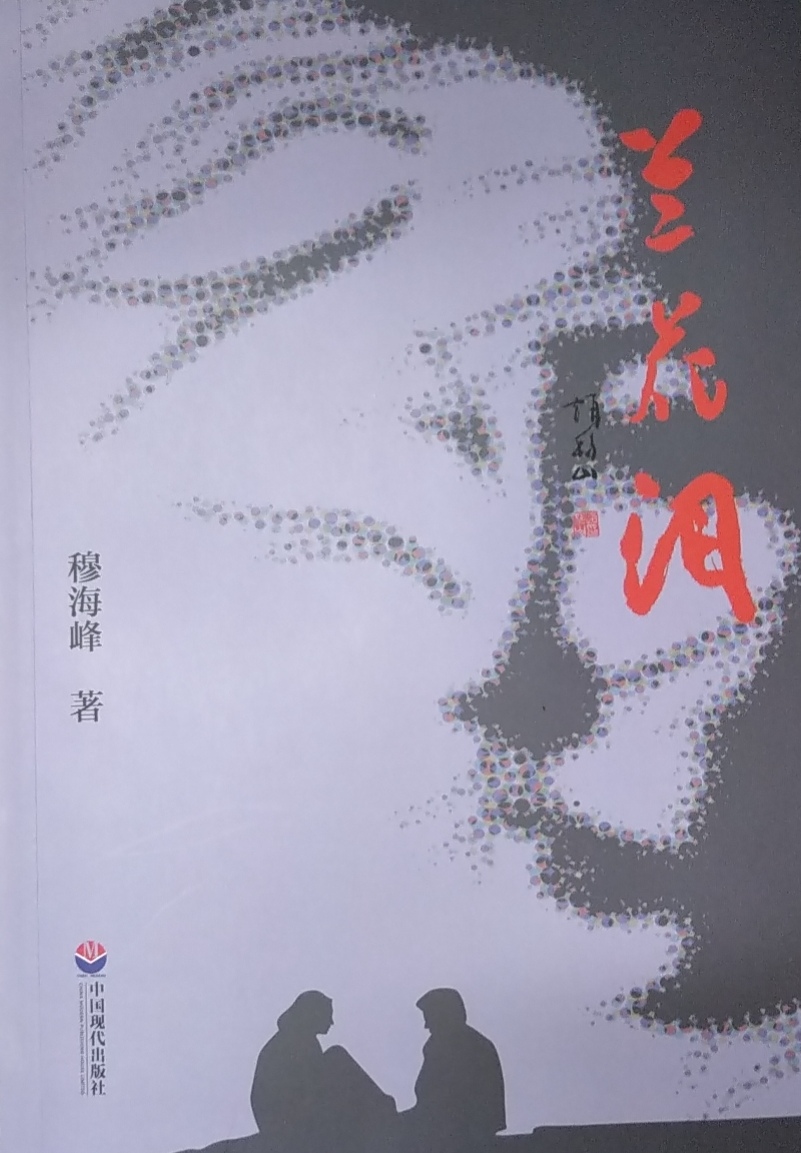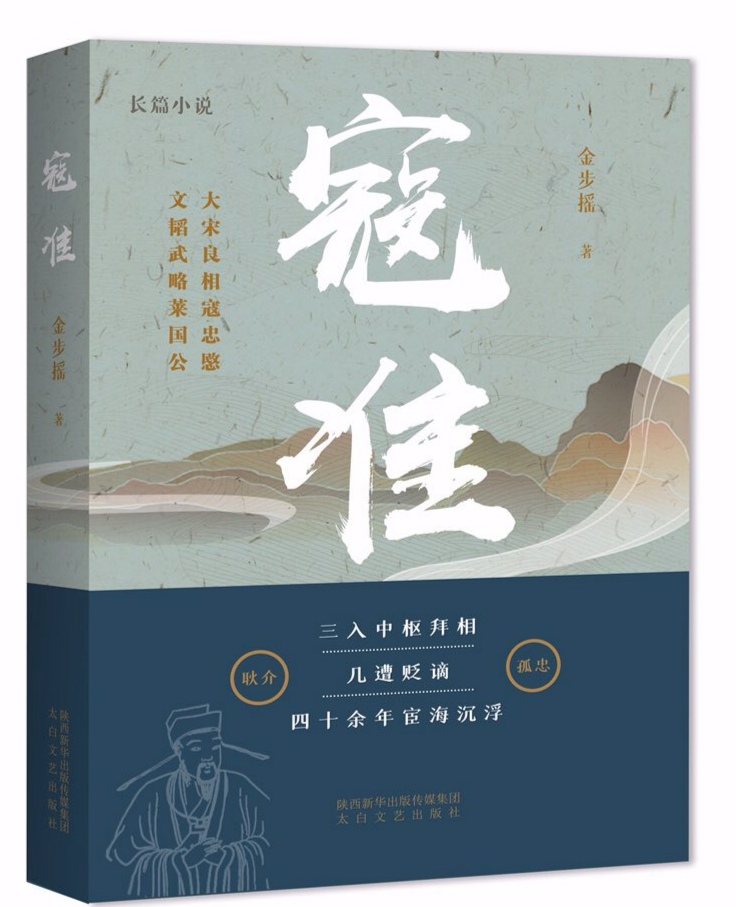落居在纺西街的和谐小区,我在纺西街散步的次数比先前多了许多。我也说不清楚散步对我身体带来的变化,只是有一种冲动,感觉到它能契合内心向外张望的需求。人跟着心灵的召唤向前走,却回到了过去。这是我今年在纺西街看到法国梧桐树才明悟的道理。
法桐是我18岁进城以后看到的。以前,我知道我是城市的陌生人,但我逐渐明白了我对故乡的记忆,那个我在乡村从未看到甚至听说过的树种,是个杂交的异国亲本。之后的若干年里,它树干高大粗壮、端直,枝条开展,树冠广阔通向高不可攀的空间井门。
纺西街的法桐,与纺西街无关。落根伊始,取表道树之义。《周语》云:“列树以表道”。所谓表道树,就是这些行道树,其目的是把道路同周围的野地区分、界划和标识出来。固土、遮阴、避风、挡雨、净化空气、美化环境是树的共同记忆。它从周朝站到了现在。《周礼、秋官》曰:“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行栗、行松、行柳都是行道树之一种。栽树移树总是与马路有关,树与大地是朋友,须臾都离不开。我只是看到“本为同根生”的法桐怎么就长出不同的气象来。高大者亦然端直,与同为端直者,长到半空却手掌五指一样散在空中,呈现出了不同的模样。我感到树有自己的心灵,用挺拔的沧桑换取我指点给它的部分崭新。
近些年,法桐已不作为纺西街行道树的首选,其实与行道树本身无关。行道树新添了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树种,杂以紫薇、榆叶梅、石楠等名贵花木,只是难见高大雄壮的气势,让气度减弱了不少。他们似乎是点缀,更进一步说也是陪衬,使法桐更见落根西安的无可替代。
法桐这一在自然中有规律的生命运动,在不断变化中让我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中,梧桐树已成为文化符号,从来都与凤凰在一起。《诗经》中“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凄凄,嗈嗈喈喈”,是凤凰非梧桐不栖最早的文字。及至庄子《秋水》、罗贯中《三国演义》都有凤凰栖于梧桐的说法。我说不清楚,此梧桐是非彼梧桐。我对事物的看法,只想简单再简单些。栖过凤凰的梧桐树已被引种到欧洲、美洲作为观赏树,杂交品种的法桐只是最早由法国人把它带到上海霞飞路一带,它们在城市行道树上相遇、相通、相视,及至多年后,成为相互学习的榜样。
在纺西街上的法桐仍然有着难以消化异国水土的不适,它的皮片状脱落,呈现出光滑的亲本。脱皮应该是疼痛的,疼痛恰好是应付出的代价。看不见它的皮脱落,大抵就不知道什么是年轮,是写在树身上的经历。我在法桐的发现使我不能自禁,时
时有一种冲动,感动法桐长在了我的身体里,是一经发现就一生追随的方向感。记忆的重合,时不时回味,沉浸在一种重温里。现在回溯纺西街,它的树种是多而又多,我看得懂重复,说不清长成一个模样的树只是个数的堆积,我更愿意说法桐是纺西街从时间的深处走进我的文字中,让我开始学习历史,也从枝叶擎起的岁月,将往昔从黎明搬运到黄昏。18岁,我从一个乡下人变成城里人,从一个封闭的乡下宅院搬到城里的一处房子,从那个窄窄的乡村土路走进纺西街。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到现在仍然是那个乡下孩子,只有一个乡下孩子才能够像我当初那样热爱纺织城。那是1979年秋季。我喜欢纺织城不同于乡下的一切。事实上,纺织城很小,只有十万人。但在我眼里,它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大城镇。在城里,我处于一种边缘状态。是工厂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养着我,并且是由社会和道德的支柱来维持的。通过对工厂生活的记忆,我保持着自己的真实性。
关于纺西街,我更愿意它是我的基点,脚步从曾经遥远的地方走回来,走出带着自己体温的一条长长的通道,把它走成活的。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不止一次法桐树对我的暗示。究竟什么是它尽头的东西,带着双倍的疑问,可以肯定的是,已经出现了许多写它的文字。我能够说清楚的是,我不可能重复他们的路子。
这篇文章好看吗?
是 否
已有 人觉得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