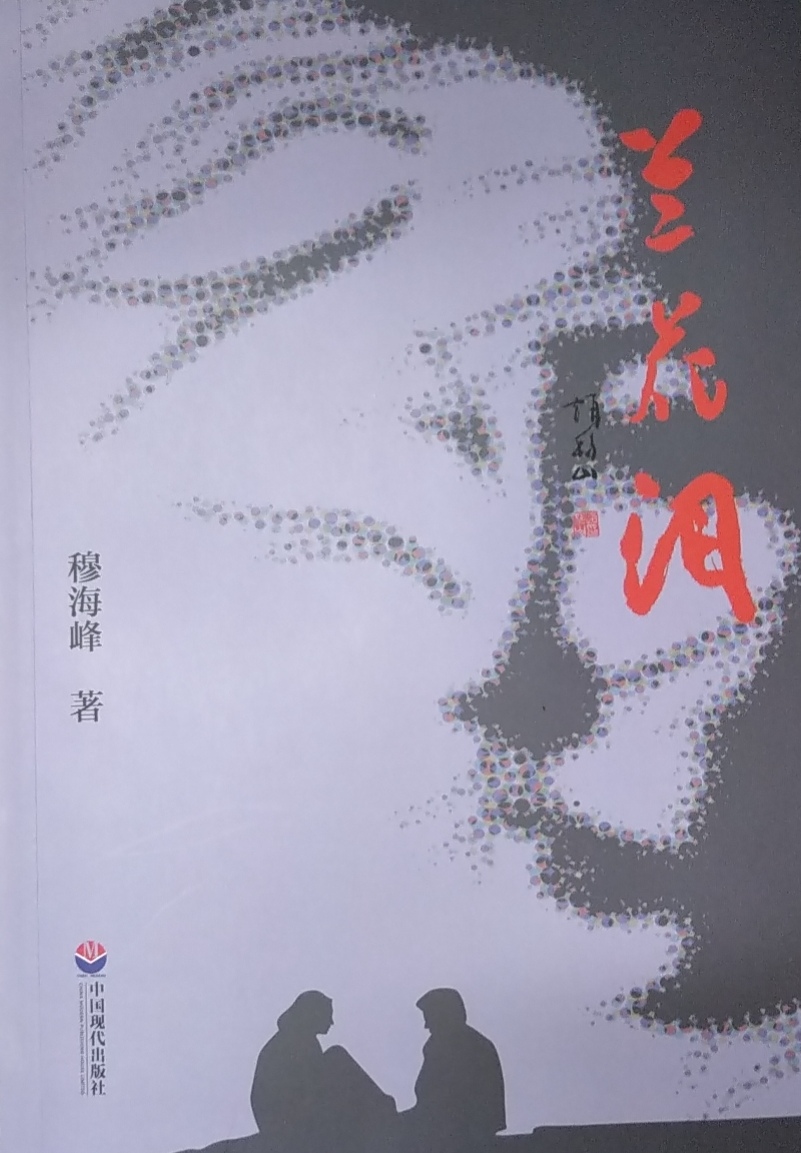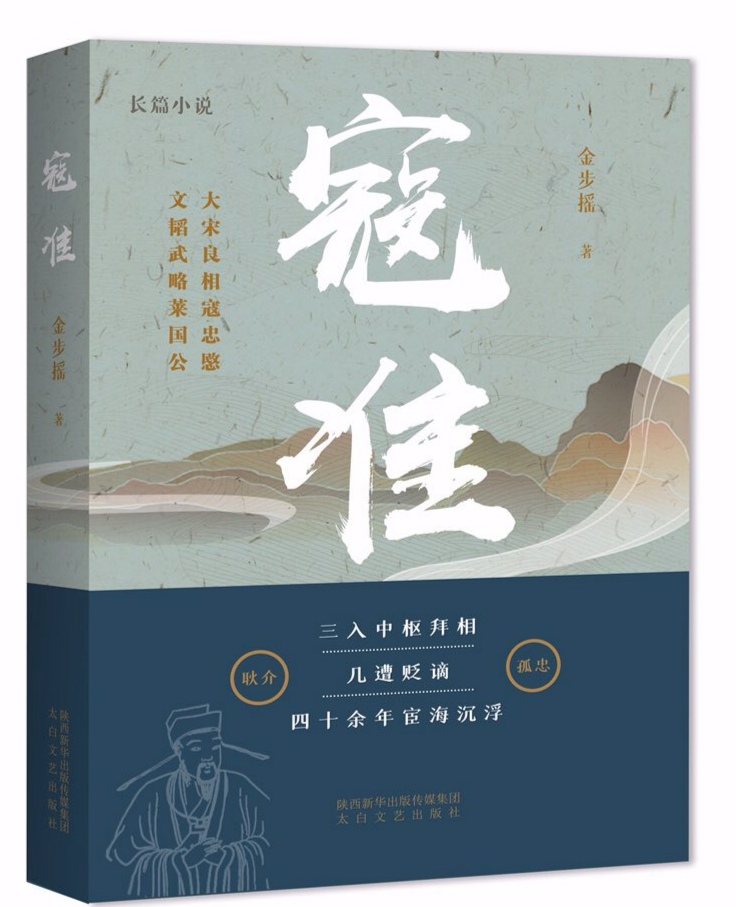白来勤
村外的打麦场北的大路南边有棵老柳树,树身之粗需我们两三个小孩合抱,树高有一丈许,这在我们小孩子心目中已算够高的了。树身上隔三岔五的长着一些疙疙瘩瘩的瘢瘤,正好助我们爬上树叉间。
我家就在村边住,老柳树距我家不到一里路,是我儿时的乐园。老柳树不是垂柳,而是枝条向上的那种河柳。也许很早的时候被人砍掉了头,所以再没长多高却长了很粗,树冠是五大股伸向四周天空的树杈,树杈间有一空间可容我们四五个小孩或坐或卧,当然被风吹雨淋日头晒的树杈间也有枯枝败叶和腐朽的迹象,还有几个土蜂窝,嗡嗡的葫芦蜂在我们身边飞来飞去,虽然也令我们恐惧过,奇怪的是从未听说谁被它们螫过。
老柳树给了儿时的我不少快乐。春天柳枝发芽,鹅黄嫩绿映入我天真无邪的双眼,我时而折下几枝柳条,从底部向稍一捋,嗬,白白细细的柳枝脱颖而出,绿绿茸茸的柳球在柳条上颤荡,我拿着它当马鞭,骑着竹马在春风中徜徉,笑意写在脸上;我时而用小刀环柳条切下一段树皮作柳笛,咿咿呀呀,呜哇呜哇,吹的春风暖融融,吹得春阳笑嘻嘻,吹得鸟儿随我唱,吹的小伙伴们着了迷,老柳树也乐得手舞足蹈......有时,我爬上树,看麦苗青青菜花黄,看父老乡亲劳作忙,看天辽地阔流水长,看炊烟袅袅夕阳靓,老柳树有时轻抚我的头,有时轻吻我的脸,令我产生无边的遐想......
夏天,黄鹂鸟歌唱,社员们龙口夺食收割忙,快打快收快入仓。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我和小伙伴们组成“红小兵哨站”,手里紧握红缨枪,头上扎起柳条帽,威风凛凛地站在老柳树下站岗放哨,宣传“麦场重地、严禁烟火”的规定,保卫“三夏”,参与到农业生产的“伟大实践中”,还侥幸地排除了个别安全隐患,受到生产队“革委会”的表扬。
秋天来了,我在老柳树上欣赏一轮新月亮,起初是远处的骊山上一只多情的眼睛闪着柔光,村庄和庄稼在月光下悠悠颤荡,时而抛媚眼的月亮飞来一个温馨的吻,老柳树敏感地伸手,推开了一泄千里的流霜。微风起兮,瓜果飘香,蟋蟀弹琴歌唱,庄稼咯叭叭拔节生长,再看天上一轮圆圆的月亮,像丰收的银锣,更像硕大的勋章!
雪花飞舞的冬天,我常想,老柳树它冷吗?它没穿衣裳。但它很坚强,在风中尽情的舞蹈,在村头的打麦场旁笑声爽朗,雪压头顶当帽戴,雪化水浸当冲凉。在我幼年的心目中,老柳树像一位老者一般慈祥,我们做了很多对它无理的事,它总是不声不响。有位不懂事的小伙伴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它的枝杈上,它竟让那名子和它一起生长!
在打麦场的南边与老柳树相对有一棵白椿树,端端溜溜的树干泛着白光,高高的树冠绿意汪汪,大概有大人们的三扎多粗、两三丈高,人们都夸是个好材料,希望它好好长。要说,白椿树离我家更近,我却不太喜欢它,因为它太高、太光、太直不好攀登,再就是它的气味也令我讨厌,所以就不跟它玩。有一年夏天刮黄风,场里的麦集堆子被吹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老柳树只是无奈的摇了摇头,少了几根头发,而白椿树则被连根拔起,脖折头碎,虽被村民们重新扶起栽端,但从此一蹶不振,第二年夏天后日渐枯萎。
我曾问爸爸,白椿树那么高怎么会被吹倒、老柳树那么低却没事?爸爸说,那是人们移栽过来的,根基浅;再加上太高就招风,最容易被刮倒。老柳树是土生土长的,根基深;再加上低不起眼,风也就无可奈何它了。爸爸还说,树挪死、人挪活,人要想把事干大干好,就不能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就得好好念书,就得走出小地方,走进大世界。当然,还不能太出头、太张扬,不然白椿树就是例子;要像老柳树那样,学会低调处世,多做实事少说话,风都拿你没办法。
几十年一晃过去了。清明节我回到家乡为父亲扫墓,顺便来到老柳树曾经生长的地方寻找童年的时光。当年的景象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鳞比栉次的楼房和城市没什么两样,宽阔的柏油马路代替了当年的田间小径,老柳树生长的地方就在路中央,听说在生产责任制后老柳树没人管护,有的人家将柴禾堆放其下,结果柴禾被玩火的小孩点燃,老柳树也跟着遭殃了,被烧得只剩下半拉,就这样它还枯木发新芽,顽强的生长了二十几年,直到十几年前修公路才将它挖掉。老柳树虽然没有了,但道路两旁却栽植了两行新柳,在春风中展示着无尽的生机和魅力,诉说着对春的绵绵情意和殷殷希冀。我眼中看到的却是老柳树的子孙们在向老柳树致礼,耳畔回荡的是爸爸朴实无华却令我受益终生的话语。
这篇文章好看吗?
是 否
已有 人觉得挺不错!
下一篇
最新文章
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