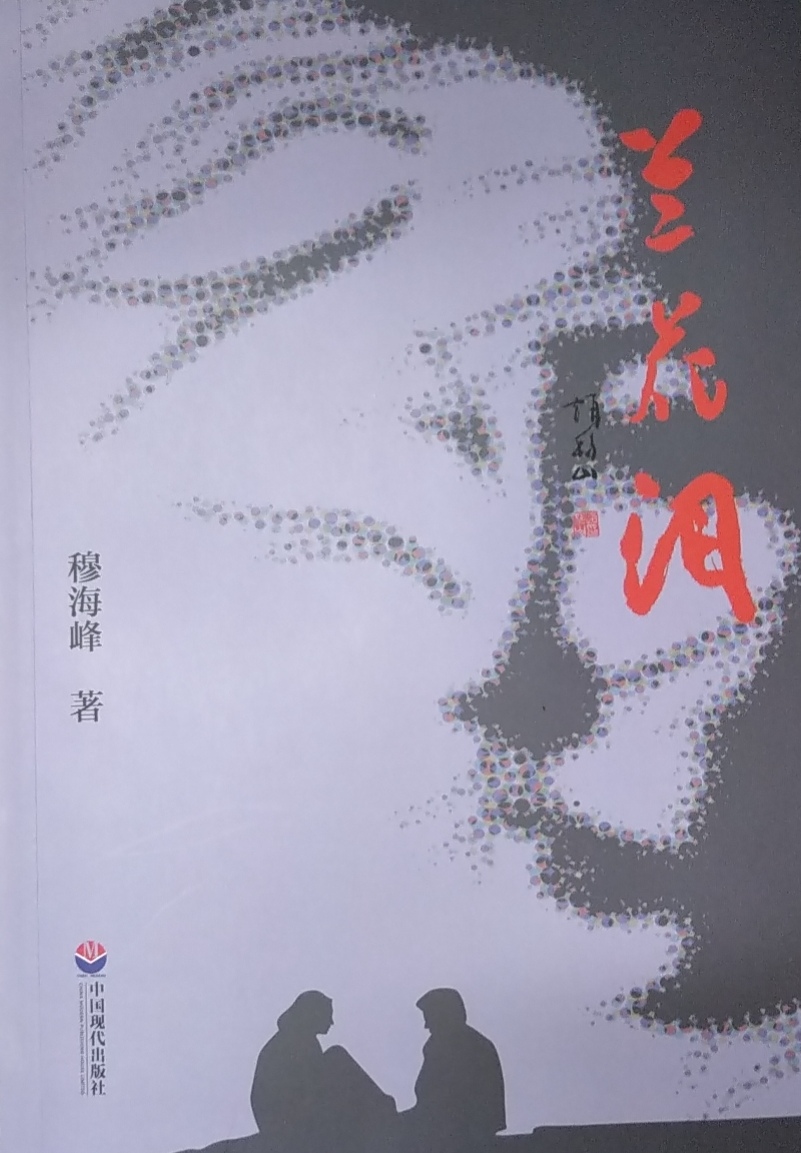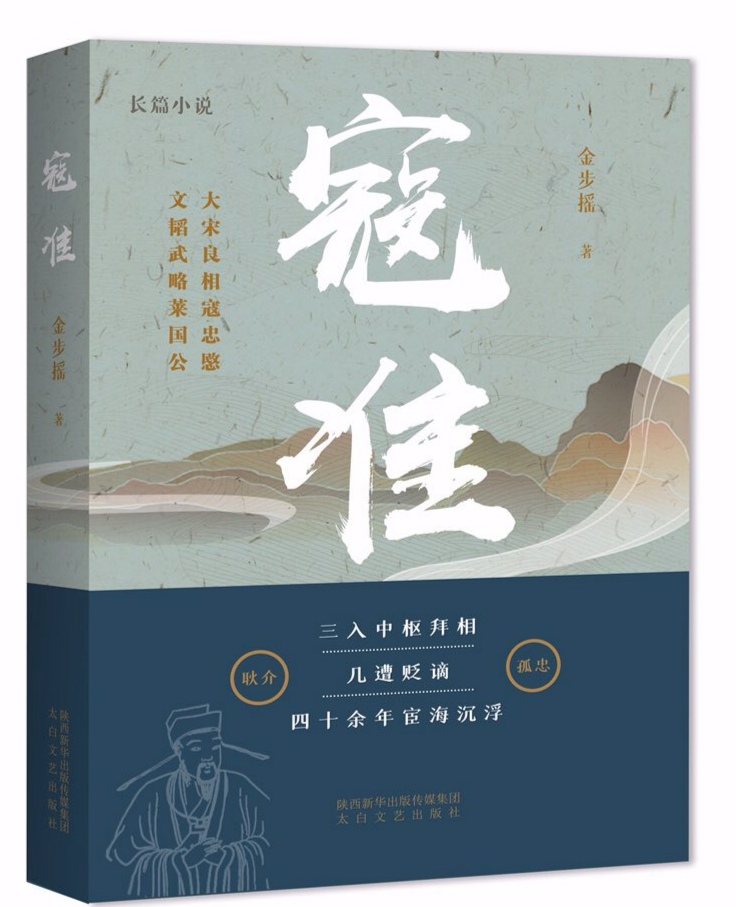路晓宇
洛河和葫芦河流淌下来,到这里汇集,转一个大弯,冲积出了一片肥沃的河地。这里叫交口河。念着似乎有点绕口,似乎是刻意起的。实际没劳神。两河在这里交汇,名字就有了,理所当然的唤作交口河。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山川不同,便风俗各异,环境造就人的性格。这里给人给地方起名字,简单直白。沿河的两边散落着一些村庄,弥家河、交口河、惠家河、杨庄河…….,似乎所有的地名都因河而生。实际上,这里还界分了陕北两个知名的县区,南边,是黄陵,是老祖宗灵魂安息的地方。北边,是洛川,是盛产苹果的地方。两县别无他物,但这两物却是国人皆知。当我的嘴唇刚刚生出一层绒毛,就带着遥远的梦想,在长途班车上一路摇晃,来到了这里,从此开始了一段有苦有乐的人生。
风景本有相似之处,一座城市有条河穿过,给城市带来灵气;有河便有桥,桥是人们往来的连心锁。也真的就有一座桥呢,就在交口河的正街上。这是我看到的最漂亮的桥。我必须用漂亮这个词。有三个桥孔,桥墩挡板一样,一截一截插入河床深处,也像一堵又一堵墙,挺立在河道上,笔直,结实,稳当。每两个桥墩之间,在上部,形成一个桥拱,与当地的土窑洞极为一致,是舒缓的、恰到好处的一道弯弧。桥面上铺着混泥土,桥栏简单,简洁,没有复杂的装饰。整个桥身整齐,平直,结构统一,浑然一体。这是一座看不出创意,也缺少匠气的桥。实用是第一目的,但又服从了关于美的最初的定义。远处观望,桥就在小镇的河上,没有拦挡感,似乎在匀称地呼吸,而且是通畅的,似乎是天然的,与河流一起生成的,是必然出现在这里的现实。
河标志了地理,把不同名称的区划连接,又起到区别的作用。对于我来说,它还在情感上提示我,河的这一边,是我生活的区域,河的那一边,是我工作的区域,具有不同的意味。而这,只有我能够体会。桥那头的方向,是我爹妈的方向。从不同方向过来,我的感受有着极大的不同。是的,很多年,一直这样,现在也如此。在我的眼里,桥不仅仅是一座桥,一座建筑,还是一个符号,一个按钮。比如我用自行车驮着妻子去医院换药,父亲带着我的孩子去翼园看鱼,妻子和我拉着手走过交口河的街道。我的一些喜悦和疼痛,都和这座桥关联着,都被这座桥知道。我不能对它隐瞒什么,在它的跟前,我可以承受,可以卸下,但是,我没有秘密。
1998年,我离开父母,风华正茂,做一个独立生活的人。我对自己的未来是茫然的,甚至,还有点恐惧。我也有一丝新鲜,一丝期待。穿上蓝色的工装,爬在单身综合楼的窗台上看着自己将要工作的企业。塔炉林立,管道纵横,一缕缕蒸汽化解进湛蓝明净的天空。毕竟,我看到了从来没有看到的,它们早就存在,我却没有去亲历,用目光一一触摸,我多么闭塞啊。不远处的桥就安静的坐落在小镇的正中央,来时的路上,我默默数着经过的大大小小的桥,带着好奇心理,也是因为无聊。记得数下来有十多座。每一座桥,都不一样。每一座桥,都跨越时空,在不同的河流的上空支撑着身子。河流有名字还是没名字,都流淌着,喧哗着。桥梁有名字还是没名字,都有一段自己的故事。其中的许多内容,都关乎人心和生死。只是,我不知道。我曾经生活过十多年的长庆桥也是一个有桥有河的小镇。在厂大门口的夜市上,我大口的喝酒,夜市顶棚很高,显得空,大,如同我空旷的心。想起来时凌晨父亲送我到汽车站黑暗深邃的天空,想起母亲走出门来反反复复的叮嘱。酒大口地喝,把心事冲进了心里。一切都将过去,未来也许就在前方。腊梅商店的柜台前,我买了一盒5元的延安烟。到夜市坐下,点了一根,大口大口吸,一下子有一种压抑情绪得到释放的快感。这之前,我以一种方式存在,这之后,我要在另一片陌生的天空下,让身体延续骨骼,血,皮肤。我的脑子,将记载下原来没有的内容。
在家里,一碗连锅面,端在手里,亲情的温暖,多么具体和可靠。可是,在父母的心中,更多的是希望,要我咬牙坚持,不要想家。我怎么能不明白呢。不久,我的身心就全部沉浸在繁忙的工作中了。这是一片广大的天地,与高耸入云的炼塔相比,我更加渺小了,也更加敏感。我成了一只忙碌的蓝色蚂蚁,停下来,触须也在摆动,身上背负着的东西,大过了自己的体重。很多东西,与我在书本上学的不同,与我想象中不一样。我要迅速消化。我和装置在一起,和炼塔在一起,和仪表在一起。调节阀、变送器、浮筒、PLC。它们,和我在一起,互相取暖。
一个人进入黄土连绵的山塬,融入鳞次栉比的炼塔中就被吸收了,似乎自己从此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事实也是如此。我身上的味道在说明,更大的改变,我不可抗拒。在炼厂,我在催化吸收稳定上班。每天在装置区穿梭,油气味满身。每天,都在体验孤独,无助。车间主任脸上淡漠的微笑,使我感觉到空洞的未来,没有归宿感,我成了游魂。闲下来的时候,如同身体被掏空一般,有时候会和班组的工友躲在仪表盘后黑暗狭小的空间里一元两元的挖坑。
家在很远的地方,父亲枯瘦的双手,母亲鬓角的白发,都是我的牵挂。那一年,我只回过两次家。即便适应了交口河的水土,我依然像候鸟一样,只有回到父母身边,我的心,才能安定下来。见了面,跟梦里一样。我似乎变得脆弱了,也许我本来就不坚强。好不容易等到春节,带着单位发的大米、带鱼沉甸甸地带回家。当我按响门铃,开门的是一脸惊奇的母亲,手上是滴着肥皂泡沫,然后大声呼喊,他爹,老二回来了。刚迈步进去,正在抄医书的父亲,带着花镜从里屋出来了。母亲慌着用围裙拭去手上的泡沫,一开口,说的是我给我娃擀面去。我放下东西,父母责怪我,家里什么都有,回来就行了,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面母亲端上来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上头堆了一堆肉臊子。吃着,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吃毕,父亲问我的工作。我说挺好的。父亲说,要学习,要好好工作,干啥事都要认真,要对得起人家给你的工资。临走,父亲送我到车站,母亲给塞给伍佰元。我说不要,发的钱够花哩。父亲说,一定要吃好,不够了再言传。我就恨自己这般的不成器,还在单位和工友赌博。车刚一走,眼泪就流了下来。
再回到交口河,心里不再茫然。工作忙碌一天,回到宿舍拼命看书,学习,发疯了的写文章。躺在宿舍单薄的床板上,幻想有一天把事情干大了,在炼厂买套房子,然后把父母接过来。好好出本书,挣点稿费,买两张飞机票,让腿脚不便的父母出一趟远门。
时间长了,熟悉了一个地方,慢慢的,也有了感情。单身综合楼的冰凉和寒冷被我记住。我还要记住,一个皮肤白净的女孩每天下班后总会在综合楼下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那是次年的五月,满山遍野的槐花开了,远近展开,高低起伏,一片片绚丽含蓄的白渗在绿色里,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香。每到这个时候,故乡的空气也是这样一般的香。
自然,有时候会和那个女孩到街上也到闲逛,交口河人不是很多,应该说当地人不多。地处渭北高原北麓的交口河本应以关中腔为主,然而这里的官方语言却以陕北话居多,尤其是清涧、子长话为盛。我初来交口河时还是比较正统的普通话,几年下来,普通话几乎不会说了,就连我根深蒂固的西府话也夹杂了浓厚的陕北腔。遇上周末,路两边摆满摊点,路上拥挤着人,还有自行车,架子车。秋天,大地的出产,似乎都集中到这里了。延川和清涧过来的狗头枣沉甸甸的,外形鼓突疙瘩,肉饱满,脆甜。宜川核桃,个头大,皮薄,肉厚,嚼在嘴里卡擦卡擦的响。尤其是面皮,让人记忆犹新。一个皮肤白皙的女人是从西府过来的,说话时声音如银铃一般,她的面皮劲道,醋香酸香酸的,辣子油红油红的,还在小锅里拌着,一股香气迎面扑来,不由得人舌下生津。她的摊点干净,人也会说话,就经常去吃。后来再没见到,听说回西府去了,家里盖了两层楼房。洛川苹果水分十足,色泽艳丽,肉质脆密,香甜可口,名不虚传。经过霜降后,苹果的糖分经过沉积,吃苹果如同喝蜂蜜。我计划好了,下次回家,一定要带两箱苹果回去让爹妈尝尝。
我喜欢吃面皮,女孩喜欢吃煎饼。子长煎饼,荞麦面粉制作,摊得很薄,也很小,二十公分长的样子,我一气能吃二十多个。用洁白如玉和小巧玲珑来形容,大致是不错的。有夹猪头肉的,有夹豆腐干的,有夹菜的,还有用精盐、食醋、大蒜片和炒熟的芝麻配置成的汤水,冰凉爽口,喝到胃里极爽。如果在夏天或是喝多了酒,要有一口冰凉酸辣的汤水,那感觉简直比当神仙还惬意。起初我吃我的面皮,她吃她的煎饼。后来我吃她的煎饼,她吃我的面皮。再后来,我们先吃面皮,再一起吃煎饼,两个人的口味渐渐一致。她带我去她家。我诚惶诚恐,心里惴惴不安。女孩的父亲拉着我的手,满口的清涧话,灿烂的笑容。我一句也听不懂,只能憨憨地笑着点头。女孩的母亲在厨房不停的忙碌着,时不时挑起门帘看我,一会一桌子菜琳琅满目的。菜没有吃多少,却和女孩的父亲喝了半瓶西凤酒。脑子晕乎乎的,就像在做梦。以后的生活丰富起来,尤其是物质生活。猪肉粉条,蒸碗肉,就连稀饭碗底也是厚厚的一层白糖。几个月下来,我竟胖了许多。
次年结婚,并分了房子。置办了锅灶,升起了一缕青涩的炊烟。再过年,孩子出生。我的女儿,也有了交口河的记忆。她喜欢周五的晚上和小朋友们在楼下花园的喷泉下玩,喜欢穿着旱冰鞋或踏着滑板让我拉着穿过交口河中心的那座桥,去一区的公园看锦鲤。她知道那家蛋糕店的糕点好吃,或者德克士关门了,又新开了一家哈比勒。
妻子产后一场医疗事故身体轰然崩塌。孩子尚小,我和妻子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情,举手无措,因为我们还是大孩子。父母来了,给我做饭,帮我照顾孩子,全家人淹没在世俗而又真实的生活中,我每天用自行车带着妻子去医院换药,回来烧热水给妻子药浴,天空灰蒙蒙的。
交口河,正由我被动地添加着内容。其他地方,慢慢在记忆中淡忘。我回家见父母的次数,也没有原来那么频繁了。但心里依然和父母在一起,很多时候填写家庭成员,依然把父母兄弟列在其中,突兀间发觉自己错了。在炼厂,有不少西府人。经常的,在春节前,约上一起走,或者在车上就碰上了。平时见面,问最近回家了吗?这是一个必然的话题。现在呢,见面,问娃学习好吗?是的,都有娃了,娃也长大了。由自己对娃的一份感情,想想父母对我的挂牵,明白人一辈子,春夏秋冬都要经历,内心还是会浮出一丝惆怅。
交口河在我的生活里渐渐真实清晰,沉重。妻子如我一般,每天为柴米油盐,为一日三餐,为孩子忙碌着。父母偶尔来,母亲一来就不曾歇下,要么翻箱倒柜整理衣物、要么到厨房顿顿做肉。她一边替我缝补纽扣,一边埋怨我,衣服洗湿糙了,都这么大的人是还不会照顾自己的生活。其实那些衣服我早就不穿了。父亲话少,知道我们已经大了,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默默地帮我维修门锁、液化气灶、地板,总之从来就没有闲过。每到假期,孩子便送到父母那里去。头一回离开交口河,女儿可能没有印象,但数次的往返,女儿便记住了交口河,知道交口河的另一边,生活着疼她的人。隔代的爱,更像孩子和孩子的交往。是的,当父母一天天衰老,情感的流露,似乎回到了童年。这更让儿女伤感,而珍惜每一寸和亲人相处的光阴。父母盼望儿女长大,女儿愿意代替父母的伤病,人生的无奈,潜伏在日子的深处,总会露头,都是上天安排和调度,不可扭转。女儿能明白这些吗?当她也有了自己的天地,她会有我这样的焦虑吗?我只是希望,女儿拥有的幸福,在源头,就丰沛不息。
08年我在西安工作,一个人,前途未知。自己最牵挂的人都在交口河。妻子的身体不好,胆结石手术也是一拖再拖。孩子的功课,家里的水电,都是我所牵挂的。父母自从我去了西安,几乎成了交口河人,每天上街买菜,接送孩子,辅导女儿功课,他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在孩子心目中,我只是家庭的一个过客。于是每周都盼望时间早点过去,早点回家。车驶出西安北郊,刚上高速,我的心便开始微微的悸动。车在关中平原上行驶,公路两边的景色被被一一甩在身后,到了铜川路正好走了一半,越过铜川开始上慢坡,连绵起伏黄土开始映入眼帘,越过黄陵,从阿党下慢坡,远远地看见笼罩在烟岚里的炼厂火炬,心里的水分开始增多,想象自己推开门妻子的拥抱,孩子的亲吻,一家人暖暖地坐在地毯上的调闹,和温暖的灯光。某个周末我回来发现,妻子变化很大,不是我当年敬仰的女神了。那时的她,纯洁,清丽,稚嫩,如今的她,应付着生活,周全着日月的水火,成熟,节制,大方,只是身体已肥胖臃肿,面容显出老相。再次拉着她的手,略显粗糙的手,我心里满是愧疚。父母近几年一直在为我的生活忙碌着,他们已经老了,到了承受的极点。
于是就考虑回来,过平常人安静的生活。年底再次回到交口河,已是深秋,苹果已经收了,杨树飘落一树金黄的景象,让我的身心,被淘换了一次。秋风瑟瑟,柳叶絮絮地翻着滚落下,徘徊在交口河的河岸上,来回地走,未来自己无法掌控,冥冥中觉得自己走错了路。没经我多想,便淹没在繁忙杂乱的工作中了。
在石化厂,我依然是一只忙碌的蓝色蚂蚁,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就连中午也鲜见回来,工作中都要一路小跑,几天几夜回不了家,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何况家庭。家里的事情全部拜托父母和妻子。父母于前年搬到西安了,家离得近,我却很少回家。父母不忍,孩子送到了他们身边。我忙,妻子常常下西安看孩子,家里的女人不在,我像狗一样的活着。下班回来在外面的小饭馆草草填饱肚子,然后窝在沙发看电视,直到睡着。或者和一帮同事喝得酩酊大醉。衣服也是穿一件换一件,堆在床头。
父母一天天苍老下去,母亲已爬不动我所居住的六楼,擀面也吃力。丈母娘也搬家到西安了,已经不能走路。父亲依然在帮我在照看孩子,精神已大不比以前。偶尔回家,父母依然笑容满面,但我心里苦楚。时间要是能停住,该多好。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女儿转学到了西安,半年时间她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不太愿意再回到交口河。迟早,她也会离开我,也会出门远去。我并不希望她永远陪我生活在这里,只是希望她不要忘记,交口河,对于她,同样也是重要的。
这篇文章好看吗?
是 否
已有 人觉得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