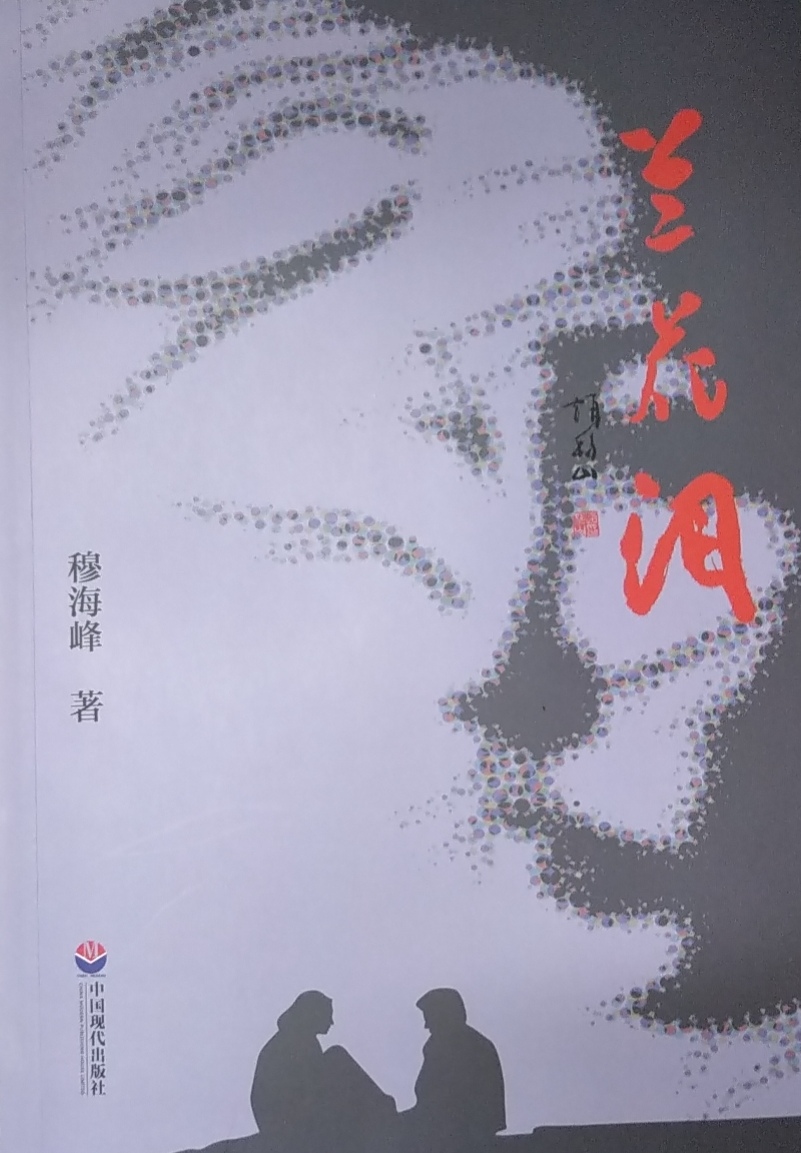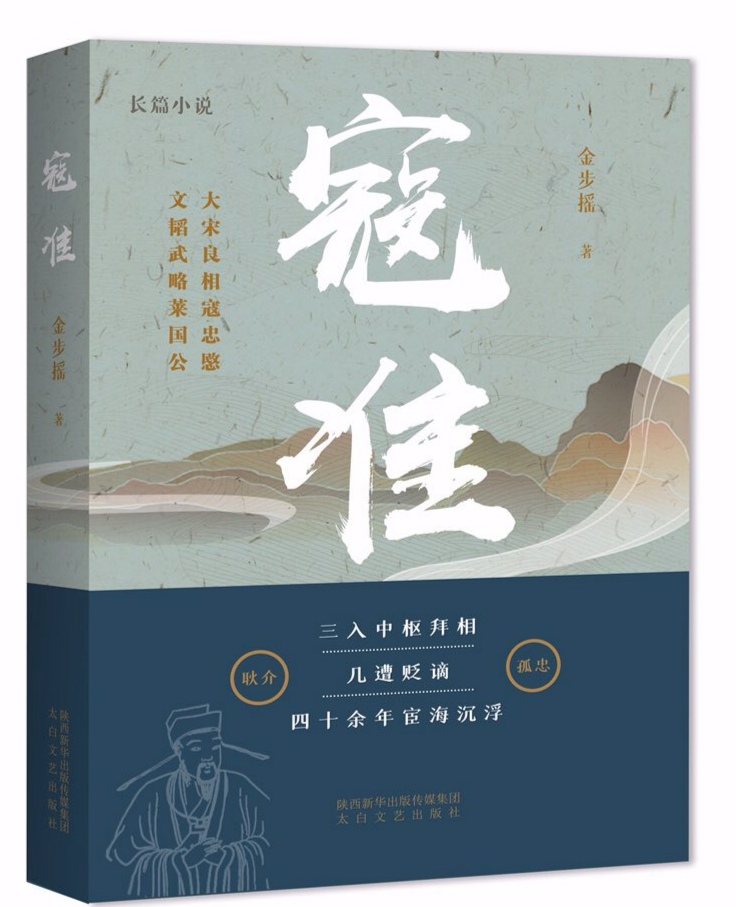春节后的一天早晨,我打通了陈忠实先生的电话。
互问“新年好”后,先生问我有什么事儿。
我说:“给您拜个晚年!”
先生说:“谢谢,谢谢,我给你拜年。”
我说:“我想上您那儿去,今天有时间吗?”
先生爽朗一笑,说:“免了,免了,这就不必了,现在时兴电话拜年,再说后天咱们就见了。”
先生的脾气我知道,只好直言相告:“有两个外地读者买了《白鹿原》,书寄到我这里,想让您签个名儿。”
先生问:“外地的?”
我说:“是北京的,也是作家,很喜欢您和您的《白鹿原》。”
先生说:“那你来,现在就来。”
去年冬天去北京出差,见了《工人日报》文化周刊的刘建民,刘建民是我的老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几位作家。其中有一位叫韩三洲的,听说我是陕西人,即刻问我是否认识陈忠实。
我说认识。
韩三洲握住我的手,忙说:“好啊,好啊,这就好了,您帮我请陈忠实签个书名好吧?”
刘建民说,韩三洲喜读书,爱藏书,有一年曾被评为北京市的藏书状元,仅《白鹿原》就有好几个版本。
这个晚上,我们在附近一家蒙古餐馆聚餐,喝了不少河套烧酒,吃了许多草原牛羊肉,谈陈忠实、路遥、贾平凹,谈《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废都》,听他们评价陕西这些大腕级作家和作品,距离就更近了。话到高潮时,河北的唱了评剧、北京的唱了京剧、河南的唱了豫剧,我也吼了几声秦腔。掌声、笑声、酒杯的碰撞声,一直持续到很晚。临分手时,大家热泪盈眶,拥抱作别。
回到陕西第三天,单位传达室师傅送来一包书,打开一看,我才想起那天韩三洲要我找陈忠实替他签名的事情。这韩三洲果然爱书,三本《白鹿原》虽然已成旧书,依然没有揉摺的痕迹。韩三洲同时寄来他的新作《动荡历史下的中国文人情怀》,这是一部读书札记,书中钩沉索引,不仅揭示了鲜为人知的人物秘辛,还给人们带来审读历史的另一种视角。作者在书的扉页写了一首诗:燕市悲歌共酩酊,秦声凄越不忍听,天涯何论初相识,书生交谊文字轻。掩卷品味,我又想起了那个晚上的聚会。
迎着寒风,踩着稀稀落落的鞭炮声,我敲开了陈忠实先生的屋门,先生一人正在看国际足球比赛。先生和我说着话,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电视机的屏幕。很早以前,就有人说陈忠实喜欢抽巴山雪茄、听秦腔、看足球比赛,看来是真的。我只能等候。
过了一会儿,先生问我:“书带来了?”
我说:“带来了。”
先生问:“有新买的么?”
我说:“有。”
先生说:“有,就快把塑料皮子撕了,准备好,让我把这点儿看完。”
我说:“你看你看,不急。”
先生说:“你弄好往书案子上放,我就写。”
我把带的二十本《白鹿原》放到书案上好一会儿,陈忠实才恋恋不舍地走进了书房,提起笔一笔一画地在书的扉页上开始签名。先生签完书名,又在他姓名后面盖上了鲜红的个人名章,然后在那地方盖上早已准备好小纸片儿以防洇染。
签完名后,先生招呼我坐下喝茶。
我问他最近忙啥,他说:“没忙啥,看看书,写点儿东西。”说着就笑了,满是皱纹的脸上就开了花。
我未多做停留,把签了名的书收拾好后就和先生告别了,时间对先生来说实在太宝贵了。(周养俊)
这篇文章好看吗?
是 否
已有 人觉得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