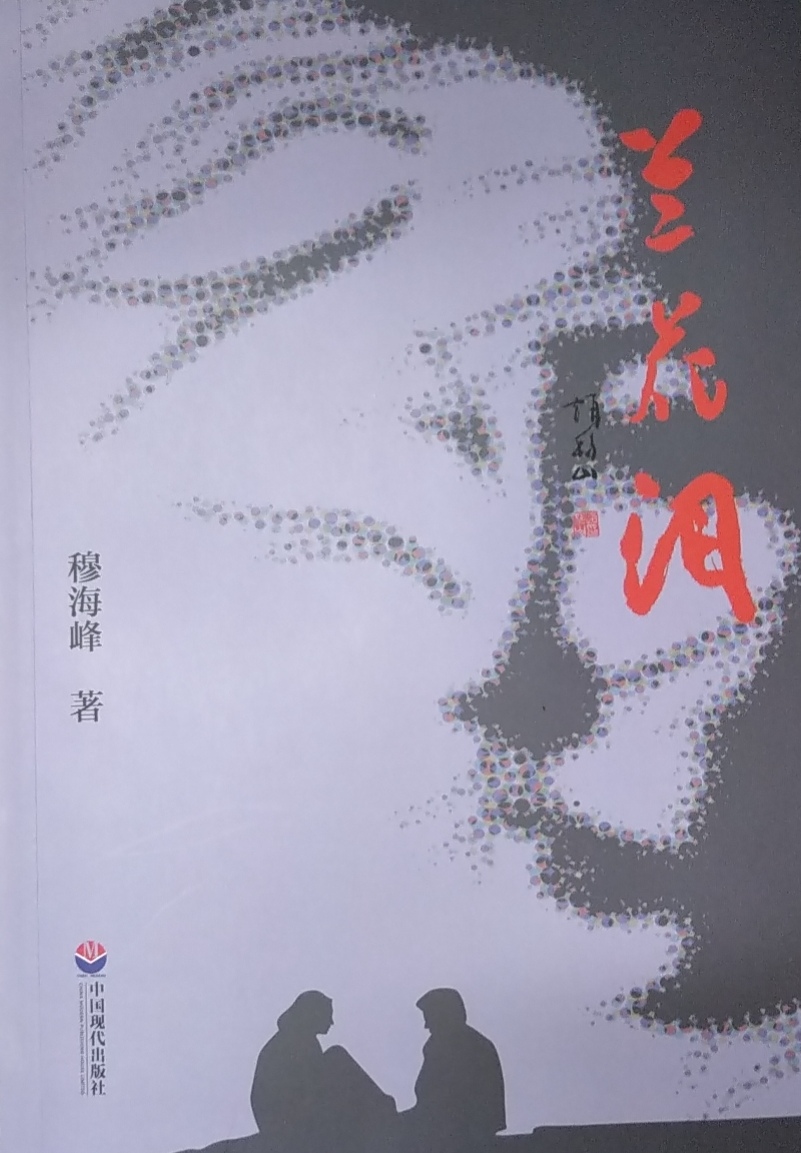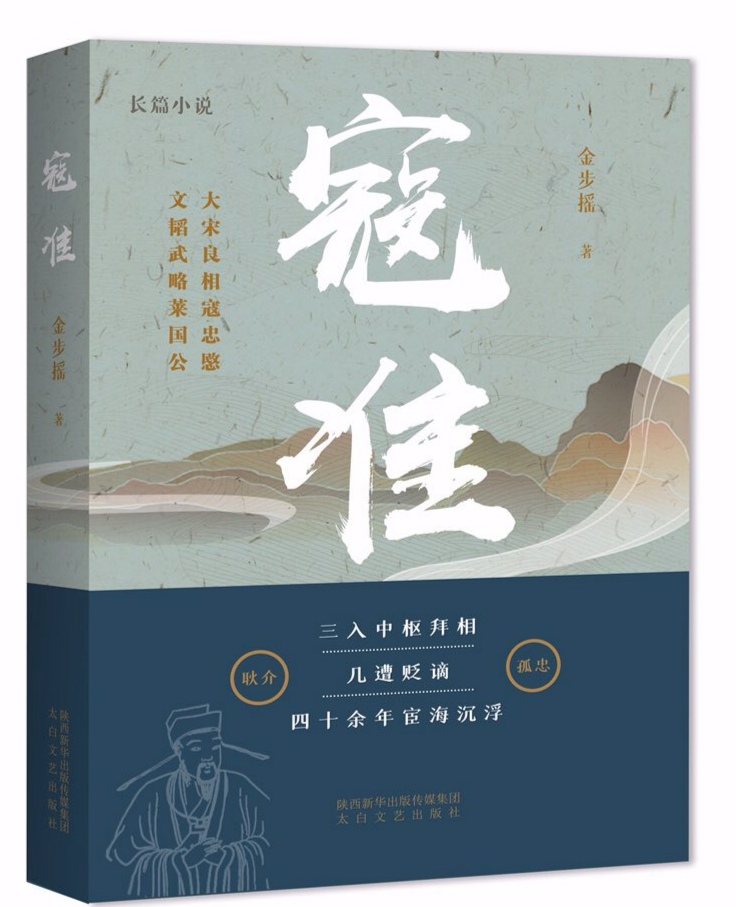周养俊
那年秋天,我们去陕甘宁交界处一个叫张崾崄的镇子上采访,清晨就从定边县城出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
张崾崄在大山深处,沟壑纵横,生活在这里的人吃的几乎都是窖水。估计天要下雨、下雪了,人们就急急忙忙去扫地,然后把雨水、积雪储存在挖好的水窖里,沉淀一段时间除去漂浮物,再让人饮用。
这里关于吃水的故事很多,笑话流传的也不少。其中一段民谣这样说道:“上了张崾崄,凉水拌炒面,要是犟点嘴,只给你炒面不给你水。”
我们是乘一辆北京吉普车来到这里的,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扭麻花似的前进,我们全身的骨头散了架似的难受。可是,一想到明天早晨要返回,大家都想看看这个不容易来的小地方,擦了一把脸就又出了旅馆门。
张崾崄镇很小,也就二三十户人家的样子。出了小镇是弯弯曲曲的土路,小路的尽头是山梁。约摸十几分钟,忽然听见有沉沉的驴蹄声和“叮当——叮当”的铃子声,循声望去,见对面山梁上出现了一队毛驴,它们整齐地走着,一头跟着一头,保持着相同的距离,踏着一样的蹄步。已经不很强烈的阳光把远山近峁,还有那些毛驴照得一片金黄色。
这一景观吸引了我们,就问路旁捡柴禾的一位老人,这毛驴来自哪里?要去何处?老人眯着眼睛望了望远处,很认真地告诉我们,说这些毛驴是驮水的,从大深沟里来,向各自的家里去。
老人见我们感兴趣,又说毛驴驮水差不多都在每天黄昏时分,没有人牵引,也没有人跟随,一头紧跟着一头,驮水时的秩序从不错乱。有人曾试图改变这支毛驴队的次序,最终都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很想不通,说这没水吃的地方的毛驴为什么和这里的人一样倔强和循规蹈矩。
我们加快脚步走着,很快就发现毛驴队后面就是那条大深沟。沟光秃秃的,沟岸和沟坡上没有树也没有草,只有沟底似乎有星星点点的绿色。我们正低头走路,忽然从沟底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震得我们的耳膜发颤。
走到沟底,我们发现两个男子站在井台上摇辘轳,井台是用石头砌的,大约半人高,井架好像是用钢焊接的,辘轳是铁制的,用于绞水的是一条又细又长的钢丝绳。摇辘轳的两个男子个子都不高,长得却敦实,黝黑的脸上滚着汗珠,粗粗的胳膊也一层汗水。在“嘎吱——嘎吱——”的声音里,随着井绳的伸缩,辘轳的转动,一桶清凉的水从井里出来了。绞水的男子很快把桶里的水倒进毛驴驮的水桶中,毛驴背上的水桶满了,一男子就用力在毛驴的屁股上拍一下,然后喊一声“得起——”,毛驴就抬起蹄子向沟上面走去了。
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从深沟里走了出来,大家没有人说话,看似心情都比较沉重。
走了一段路,不知谁第一个回过了头,于是大家一齐转过身,眼睛又直直望着对面的山梁。
山梁上移动着驮水的毛驴队,响着毛驴“踢踏——踢踏——”的蹄子声和“叮当——叮当——”的铃声。
旷野里静寂无声,毛驴的蹄声和铃子声更加清脆和辽远,渐渐地,我不再觉出这声音的美感,而是愈听,脚下的步子愈发沉重,那声音好像每一声都响在我的心上,有一种说不出的痛。
这个晚上,旅馆的老板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年,这里来了个驻队的年轻干部,这干部不像以往来的干部,既不给大家讲大道理,也不经常组织社员开会、学文件,他每天背着干馍和水壶,奔波在山峁上、深沟里。后来,他接来了几个城里人,那些人穿着风衣,戴着太阳帽,拿着笔杆、望远镜什么的,在大深沟里测呀画呀算呀,最后终于在沟底发现了水源。水井打成了,老百姓吃上了甘甜的水,虽然水井在深沟里,每天还得靠毛驴来驮,但毕竟结束了张崾崄镇百姓吃窖水的大问题。人们正想着能不能多打几口井的时候,打井的驻队干部却病了,住进医院就没有出来。
“好后生啊,真真地可惜了!”旅馆老板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夜深了,四周静寂得出奇。
我想象着那个年轻驻队干部的模样,耳边又响起了毛驴的蹄子声、铃子声。
这篇文章好看吗?
是 否
已有 人觉得挺不错!